父母唔惜奴,
放囝摸缶土,
所行甕礪路,
所沃風時雨,
所做斷晏烏。
上面這首流傳于楓溪的民謠,道不盡舊時楓溪陶瓷行業童工的艱辛。小孩子不懂父母的苦楚,埋怨父母不疼愛自己的孩子,讓自己小小年紀就去陶瓷廠做工(潮語“奴”、“囝”,指男孩,“缶”潮俗指陶瓷)。勞動環境惡劣,走的是鋪滿陶瓷碎片道路(“甕礪”潮語指陶瓷碎片);勞動強度大,做的跟大人一樣,陣雨(風時雨)一來,就要到屋外空地搶著把晾曬的“缶坯”搬回屋里;勞動的時間長,晚上要做到伸手不見五指(“斷晏烏”)。
舊時招童工的也不少,有一說民國時期童工占總用工的三成。當時楓溪鄉里多數家庭供不起孩子念書,孩子十歲左右,就送去“做厝”(即工場)當“師仔”(“師”潮音讀如“西”,“師仔”即徒弟)。楓溪俗語“從系裙圍做到舉竹槌”(“舉”潮音讀如“居”五聲),意思是從童年一直干到老年,指的就是雇用童工的現象。陶瓷行業的執業者多數既是老板,又是師父。作為父母的,找一位當老板的親戚,請求收其孩子為徒弟,指望孩子勤做力學,成長為“師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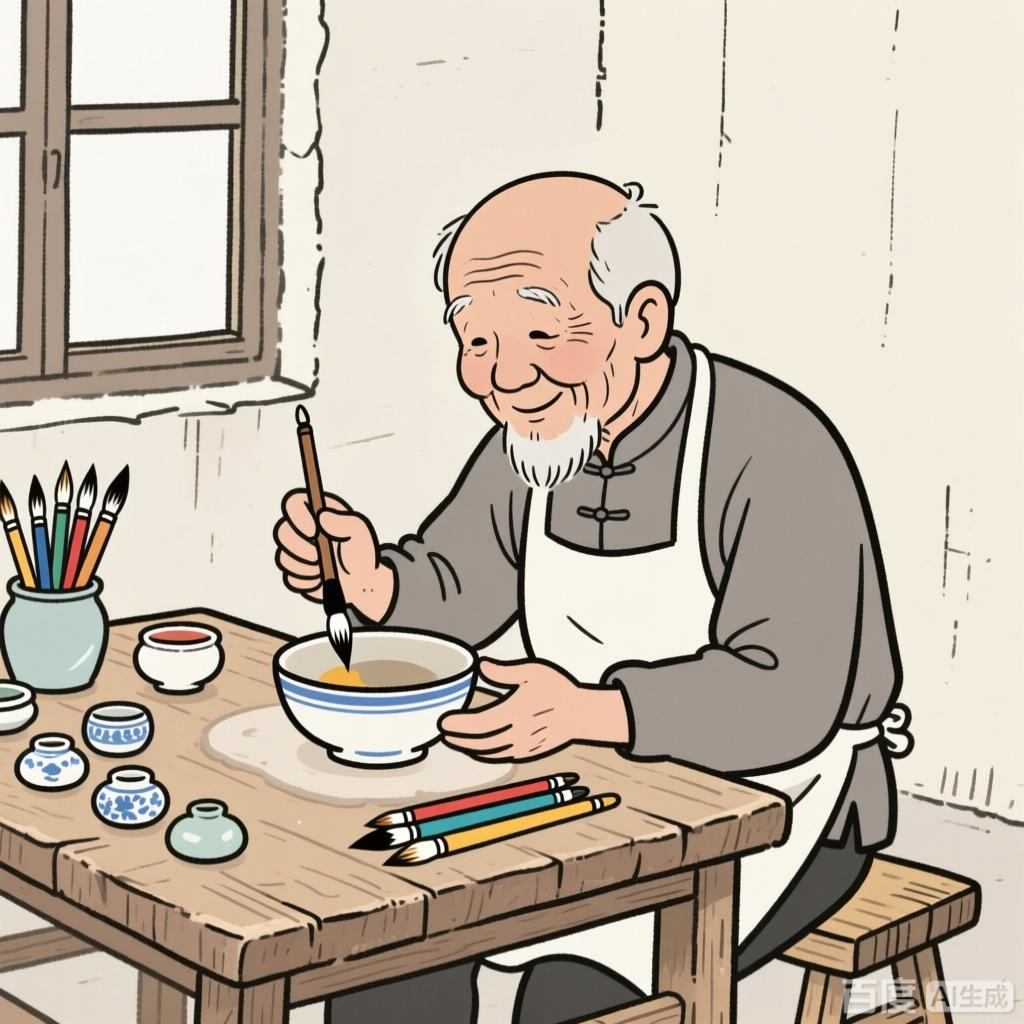
當“師仔”自有一番苦楚。陶瓷行業的“師仔”,一般是做“落車”師父的下手。從前陶瓷行業的成型工序,普遍采用手拉坯,俗稱“落車”。車,就是一個直徑約1米的蘑菇形竹木泥土制成的轉盤,用腳在上面旋轉,帶動轉盤轉動,將瓷泥團放在轉盤中間,隨轉盤旋轉,師父在泥團頂端邊捏邊拉,按規格尺寸拉出“缶坯”,或盤、或碗、或杯。負責轉盤轉動就是“師仔”的工作之一。勞作之時,雙手撐在“土車”旁的“土椅”上,左腳撐地,右腳帶動“土車”轉動,隨著轉速越來越快,最后右腳用力一踢,離開“土車”,所謂“挨車踢”指的就是這一腳。“師仔”的另一項工作,就是“土”(“”潮音讀如“深”八聲,指用手揉和)。從前沒有機械練泥,只好用手工,除了用腳踏,就是用手。一團瓷土,重量在20斤以上,放在“土椅”上,反復旋轉揉壓,經過半個鐘頭,揉成“土庵”(泥柱),才可以上車拉坯。
這反復旋轉揉壓,得花“師仔”多少力氣!一團瓷泥成,氣喘呼呼,汗流浹背,干脆赤膊,只留一條褲衩。這一動作,俗稱“土攆”,故楓溪人戲稱:“挨車踢”和“土攆”,是楓溪拳路的二步絕招。
“師仔”在師父的指導下,憑著自身的驢拼,靠著自己的領悟,十年八年之后,或許就能出師,成為“落車”師父。
作為家長的,總希望師父對自己孩子嚴格管教,早日成才。但不是每名師父對孩子都會“嚴條”(嚴格),出于對幼小孩童的保護,有的師父對“師仔”就比較寬容,楓溪橄欖巷的“大成伯”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民國時期楓溪有一首童謠是這樣的:
大成伯個人好交卙,
晏來早去無管轄,
睡去牽被疊肚角,
肚困揢錢去宮前食粿汁,
做著畏宮前溜宮石墊竹殼。
大成伯全名謝大成,是民國時期楓溪的一個制瓷作坊業主,對前來當“師仔”的童工呵護有加,這首童謠就是最好的寫照。
上面這首歌謠,用原汁原味潮州話記錄下來,為方便理解,說明如下:
第一句“大成伯個人好交卙”,“卙”潮音讀【徐庵4】交往的意思,大成伯這個人值得交往; 第二句“晏來早去無管轄”,“晏”是晚的意思,即使童工遲到早退我也不管; 第三句“睡去牽被疊肚角”,(“師仔”有時過于疲勞)上班時間睡著了,就給他蓋被子; 第四句“肚困揢錢去宮前食粿汁”,(“揢”潮音讀【戈腰8】,拿的意思),半晌肚餓了,就拿錢去(橄欖巷附近的)大宮前吃“粿汁”; 第五句“做著畏宮前溜宮石墊竹殼”,干活厭煩了,你就跑去大宮前“溜宮石”玩吧(我也不管),記得要在屁股下面墊一個竹筍殼(不然,磨破褲底回家可要挨罵)。“溜宮石”,指三山國王廟門口石臺階兩側的斜坡石板。
看看,孩子來大成伯這里,根本不是來“學工課”,簡直是當少爺來了: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大成伯如此呵護,難怪小孩覺得他“好交卙”(值得交往)!
不過當家長的就不這樣認為了,孩子付托給你,目的是“學工課。”,古話說得好:“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要求不嚴格,孩子不刻苦,怎么能“出師”。大成伯啊大成伯,孩子被你寵壞了!
現代社會,雇用童工是違法行為,當年大成伯對童工的態度,可謂是“放飛自我”,讓兒童自由發展,健康成長,大成伯做得對。只是處于那個年代,人們畢竟要吃飯,學手藝,謀生計。對錯臧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文字 | 佘桂堂
編輯 | 翁純
審核 | 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