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潮人潮文化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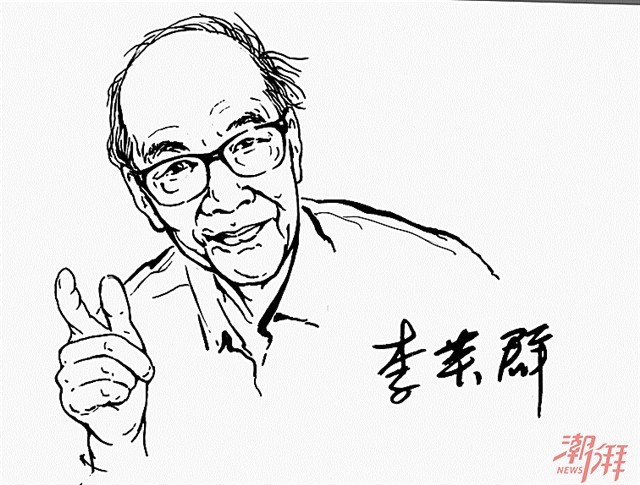
史炎來訪,他剛當選潮州市作協新一屆主席。于是,剛坐下,我們就談起文學來。
書寫潮州,講好潮州故事是我們交流的重點。講故事,因為文學即人學,當然要了解人,我就問史炎:什么是潮州人?
我們自己就是正宗的潮州人,但要講清楚潮州人,就不是很簡單的事,它不單指生活在潮汕地區的人,還指現在生活在祖國各省市的潮籍人士,更包括世界各地祖籍屬大潮州的僑胞,他們是有文化認同、有鮮明特點的一個族群,他們的人生態度、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審美趣味你真正了解嗎?他們身上的文化特質你明白嗎?
在外地人眼中,辨別個體潮州人不難:講潮州話食工夫茶,以前可能還喜歡用浴巾。不用說,這就是潮州人;對群體潮州人,外地人的評說雖略有出入,但也近似,就是重商、崇文、精致、樂天。這些,本土潮人也基本認同,
重商,就是潮人會做生意,有東方猶太人的比喻。這一稱謂本是貶義詞,是泰國六世皇對旅泰華僑某些行為不悅而借用的,但后來引用的人卻用來稱贊潮州善商。
歷代潮人中有許多成功商業巨賈,出過華人首富,如何認識并表現他們,必須抓住潮商特點。如果說成功商人都重誠信、講互利,那么天下巨商皆有這種風格,我更愿意從細微處去認識潮商。在潮州俗語中,有“小小生意會發家”“買賣算分,相請無論”流行至今。愿我們的作家對此作深入的挖掘。
崇文,就是重視教育,愛讀書。有家訓“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為證。雖說這話是南宋名相陳俊卿對宋高宗的廷對名言,是他老家莆田的家訓。我們祖先幾乎都是從莆田來的,移而用之,足見我們對“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的高度認同。不過,我們仍然希望從細處挖出潮人重視教育的獨特細節。我的文友中,不止一人提及孩提時,不識字的祖母提醒他:地上掉落有字的紙,千萬不能“厭戲”(即跨過去),要拾起,否則是對孔子爺不敬。我們中秋拜月,有一種產于留隍的云片糕,命名為“書冊糕”,也拜書冊,這是一種什么滋味,其意何在?挖吧!
精致,或者說精細。有俗語“潮人作田如繡花”作佐證,有從熙公祠門樓肚石刻那條細若火柴梗的懸空牛索作物證,更有麥稈畫為做一把孔雀尾巴的羽毛,剪了上萬根細若頭發的麥稈絲為證。這些,在國內也非絕無僅有。我更希望從潮人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地不在的工夫茶座中那三個世界上最小的茶杯中去“撈撬”,去提取潮人特有的文化品性:那是儒雅還是悠閑?
樂天,是的,潮人天性樂觀。工夫茶座中從“暹羅到豬槽”的海闊天空的神聊,有許多幽默、詼諧和機趣!在民歌民謠有多少可樂。“天頂一粒星,娶著雅又后生。三頓食飯免物配,一頭看一頭扒”“門腳一叢梨,彎彎曲曲生一個,食到醬老正娶,昨夜晚慐慐叫叫做嬡。”怎么樣,口味勝可樂。舉個時下例子吧:市郊仙田一對夫婦,那年一場臺風,不可抗拒。他家屋頂被掀翻,慘過杜甫個茅屋為秋風所破。但這對夫妻在臺風過后回來,把凌亂的家具找出部分,在墻外做飯,吃飽之后,又閑閑沖起工夫茶。鄰居過來關心,兩人笑笑地說:食了正來,飽了肚才能抗災復產!
那天,史炎在談到潮人異于其他族群的特點時,提到我曾有篇短文叫《從月娘說起》,說潮人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的品質是深藏在全體普通百姓間的。我說:“人家說冬日曬太陽,我們潮州百姓說借日。太陽公呀,不好意思,我借你一陣日來暖暖身子呀!”
史炎立即說:“人家說出海捕魚,我們潮州說‘去討海’,是向大海討一點它們的產品呀。”說完,他起身說老婆叫他吃晚飯!
這位新主席老兄,回家后飯碗放掉,又連續來了一組微信探討飯前的話題。我回他說:潮文化不是創造出來的,是人民生活中流出來的。我們要講好潮州故事,就要了解潮人,要了解潮人,就得了解潮州這一方水土。我是相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潮州的地貌值得大書特書,我們有大海有大山有丘陵有平原,有梯田、旱田、水田,有湖泊、池塘、山坑、河溝,特產何其豐富,食材何其多樣,這才有世界美食之都的問世。
于是,有了本文的題目。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