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一些現(xiàn)象,讓你難忘。以后這情景重新出現(xiàn),引起你濃烈的興趣,但又覺得沒什么意義,不宜入文,就放下了,但放而不下,它會時不時出現(xiàn)在心頭。
記得有一次與林倫倫教授聊天,他說在中山大學讀書時,聽晚年的王起(王季思)教授講課,原本普通話講得很順溜的王教授,怎么老了是滿口的溫州方言。過后他問王起教授,教授說老了滿口母語,這叫返老還童。
漲知識了。原來以為返老還童是指人老了童心未泯,行為天真,沒想還指人老了滿口講的是用母語(方言)。
忽然想起自己的經(jīng)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創(chuàng)作一部潮劇參加廣東省文藝匯演。演出后在劇本交流大會上介紹創(chuàng)作體會。講演結(jié)束,一個人趕到后臺來沖著我喊,原來是韓山師專中文系同學丘金貝,他也寫劇本,這次也有一個戲參加匯演。他直沖我說:我聽你發(fā)言,還懷疑不是你呢,怎么普通話講得這么差,妥妥的潮州普通話!說后哈哈大笑。
哦,我自己是毫無感覺。在師專時,學校舉辦普通話演講比賽,我可是被全班同學選舉為代表的唯一人選啊!
當時,我還未聽到林倫倫教授轉(zhuǎn)達的王教授這段話,否則我會回答丘金貝同學,說這是返老還童,因為我老了。
剛才為寫這則短文,去信征詢倫倫兄臺再次確認,他回信說:“是的,老了老了,只剩下母語(方言)能說得流利。長大后才學的語言就慢慢淡化了。"
那么說起來,這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
但是,在生活中它似乎不僅僅是一種無色無味的自然,是無意義卻有意思,有味道的存在!
我寫過一則短文叫《口味》,說我那位畢業(yè)后留在廣州工作的女兒從小喜歡吃潮州產(chǎn)的芥藍菜。我們叫她“芥藍佬”。現(xiàn)在,常讓我們從潮州給她快遞芥藍過去。潮安金石籍的軍旅作家,海軍出版社的總編輯林道遠讀后寫了一篇《口音》,說口味難忘,口音更難忘。寫得精深意濃,讓我一個一直生活在家鄉(xiāng)的人讀了也為之動容,能夠理解,卻無體會。
2016年10月,我到北京探親,平時多有聯(lián)系的旅京親友程福全兄給我電話,說有一個旅京潮籍老鄉(xiāng)的茶聚,希望我去食茶,我聞之欣然赴會。
哇,座中多是著名人物、劇作家、音樂家、新華社記者、中央電臺播音員、退休老干部、在讀研究生。工夫茶飄香,家鄉(xiāng)音濃濃。
談話進行到半中間,中央國際廣播電臺第一代潮語播音員丁度章拿出一張便箋,上面是他們上次聚會時合作的一首潮州方言詩,我記得最后一句是“你哩無來巧答郎”,他問我“巧答郎”有音無字,我們用這三字代之,這三個方言音大家都明白,就是“太可惜”的意思,但這方言特有的“答郎”一詞,那味道真是普通話或文言文中找不到的韻味,是失落,是感嘆,是淡淡的憂愁,是久久的難忘,是說話輕聲細語的潮人才有的口吻,妙絕了。他問我這個用方言寫作的編劇,豈知這二個字應怎么寫?
座中皆名流,譽滿京華。一個個滿頭白發(fā),今日是人人返老還童,為了一個母語方言詞,從上次聚會到今次,一直在斟酌,品味,興致勃勃,全神投入,專注著,沉醉著,滿口都是童年時說慣了的方言。這種氣氛,是任何高端的、專業(yè)的研討會所不能有的輕松,這是一種難得一遇的文化享受。
我明白,我今天奔赴的是一場母語的盛宴。
實在不能用有什么意義來評介這次聚會,但它很有意思,這就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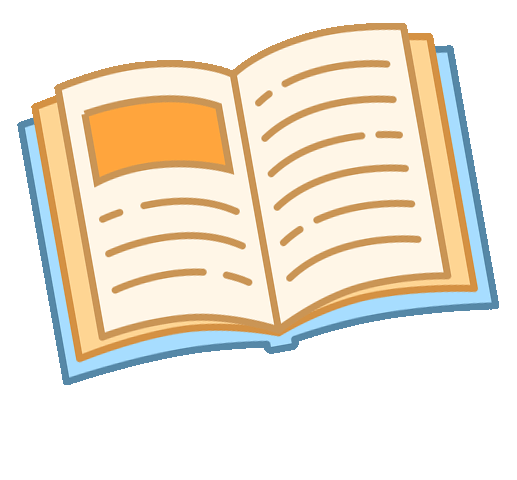
文字|李英群
編輯|翁純
審核|詹樹鴻
- 開學在即!學校周邊這些施工路段,出行請留意!
- 抗戰(zhàn)英雄人物② | “韓江赤子”鐘騫
- 潮州市區(qū):三百多面國旗高揚紀念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
- 楓江流域整治工程 | 楓江深坑國考斷面攻堅工程(潮州段)治理項目建設持續(xù)推進 經(jīng)五年治理水質(zhì)達近十年最佳水平
- 匠人匠心·非遺對話|標準只為傳承好工夫茶 ——記潮州工夫茶非遺傳承人陳輝的守與創(chuàng)
- 《智能坐便器》《輕智能坐便器》團體標準將于9月1日起正式實施 以“標準+服務+保障”推動產(chǎn)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
- 紅色登塘 光輝記憶 一座革命豐碑背后的潮汕抗日烽火故事
- 預防登革熱:一只白紋伊蚊的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