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湫寶塔話滄桑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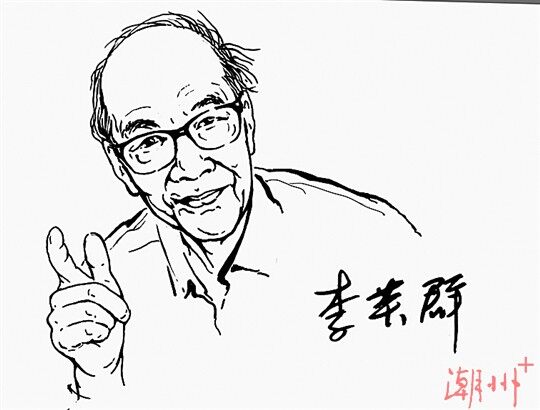
每次提及潮州八景之一,那座消失在江心水中的龍湫寶塔,我總會聯想到“二只鉎牛一只溜”這句經典民謠,冒出一句“潮州八景一景丟”覺得頗有文化趣味。
龍湫寶塔被洪水沖毀,一些潮人深感失落,就掠柑堵柿,用涸溪塔來冒名頂替,湊足八景。但鄭蘭枝的八景詩仍流行,如果在旅游圖上出現涸溪塔的圖像,配上鄭蘭枝的詩,就顯得不倫不類,甚至很滑稽。
對這種現象,魯迅先生稱之為《八景病》。他在《再論雷峰塔之倒塌》一文中,稱大部分中國人有《十景病》《八景病》,認為是形式主義,不能實事求是。
對于用涸溪塔冒名頂替龍湫塔,廣大潮人,尤其是古城市民并不太在意,不關心,顯得很寬容。他們并沒有提議把那只被洪水沖走的鉎牛找回來或重鑄一只,而是用“二只鉎牛一只溜”的民謠來表達自己的審美情趣。
1991年6月,因天旱,韓江水位降至8米,江心露出一堆礁石,據考即為“龍湫寶塔”遺址。有熱心人建議修復古塔,還擬出修復方案。但反應平淡。市民就像對待用涸溪塔頂替一樣,不太在意。
我很贊賞潮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市民總體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水平。他們明白,潮州八景是一種歷史存在,消失了的龍湫寶塔也永遠是一種歷史存在,它的藝術價值會成為市民永久的文化記憶。鄭蘭枝撰八景詩是在清乾隆年間,龍湫塔早已坍塌不見,他面對水中遺址,憑聽聞和閱讀的知識,展開想像的翅膀,抒發心中的詩情。這首詩,較之于有實物存在的金山古松和韓祠橡木,抒情和詩意卻更濃,古松頌忠節,橡木唱文脈,而古塔更具浪漫色彩,更有詩的韻味。我們恰恰不必為它的消失遺憾。從文化藝術層面上看,這種消失更有豐富的內涵。蘇東坡的《赤壁懷古》如果他寫的是火燒赤壁現場,絕不可能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放和“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 檣櫓灰飛煙滅”的霸氣。我們可就沒這首豪放派的千古絕唱可玩賞了。
我們還可以從崔護的“人面桃花”中獲得同樣感受:“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依舊的笑春風。”注意,他寫的是去年的艷遇,如果讓他去年就寫,肯定寫不出這般味道。這一年重來,我們可想像到他有多少難眠之夜,對今日重來設想過多少美好,今日一路前來又是怎樣的忐忑不安。怎樣?很豐富吧?
潮州人并不在乎一景一物的消亡,歲月無情,大浪淘沙,白云蒼狗,滄海桑田,再正常不過,正所謂人間正道是滄桑。失去一只鉎牛,得到一句將會千古傳唱的民謠,充滿文化趣味,展示了潮人的幽默與樂天!
主張修復寶塔的人也許會問:“那我們近些年為何要修復湘子橋、牌坊街?”問得好。我也想問:“為什么呼請修復龍湫寶塔,市民反映清冷;一聽要修復湘子橋和牌坊街,市民熱烈響應,出錢出力?”
當年,因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需要,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橋亭和街亭進行人工拆除、現在條件變了,我們有能力了,所以進行修復。
我并不反對修復龍湫寶塔,對古文物,古建筑,有關部門一直在努力修復,并做到修舊如舊,像明城墻府城樓等等。
我寫這則閑文,只是為品賞一點文化趣味。
編輯|郭洵汐
審核|吳燕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