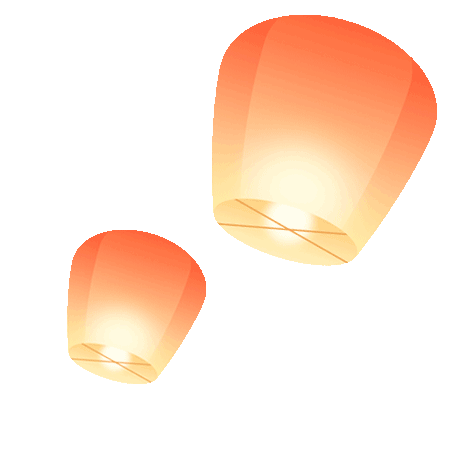
但愿人長久
□劉妍
畫家愛畫荷,老百姓家里愛掛荷。屏風(fēng)、隔斷、背景墻,入戶花園、餐廳、書房,無處隱藏,八面而來的“荷風(fēng)”,拂面暖心舒心。“荷”通“和”。以畫潮劇“臉譜畫”著稱的許固令也愛畫荷。
杖朝之年的許固令從廣東汕尾走出,漂洋過海、披荊斬棘。他是海之子,是當(dāng)代華人畫壇上的巨擘,在國內(nèi)外美術(shù)界享有盛譽(yù)。林風(fēng)眠、關(guān)良、韓羽、丁衍庸等畫壇巨擘,都曾在中國戲曲人物畫的路上積極主動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以意象畫表達(dá)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戲曲中的人物臉譜,許先生尚屬國內(nèi)第一人。許先生荷花系列作品,側(cè)重關(guān)注中國人文精神的研究與價值的傳遞,注重個體內(nèi)在的精神表達(dá),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中國畫藝術(shù)語言的表現(xiàn)特征——以形寫神。許先生的審美角度不再單一和狹隘,用西方人熟悉的繪畫語言筆觸,另辟蹊徑,表現(xiàn)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人文內(nèi)涵,實(shí)屬在探索中西方繪畫藝術(shù)的完美結(jié)合表現(xiàn)。曾經(jīng)只作為傳統(tǒng)國畫藝術(shù)形式的代表——水墨理念,被許先生大膽地嫁接和運(yùn)用在當(dāng)代中國畫創(chuàng)作實(shí)踐語境中。作品不是簡單地運(yùn)用畫語言、筆觸表現(xiàn)中國水墨畫,而是中國文化精神、民族審美心理在新時代與時俱進(jìn)的結(jié)果。無論何種教育背景、地域文化特征的觀眾,在面對意象臉譜畫或荷畫時,看到的是千人千面,看到的是人生海海,看到此岸彼岸,極易獲得共情和共鳴。
說著說著,許先生提及另一位愛畫荷的朋友程小琪。的確,我上一次見程小琪,還是10多年前,在廣州畫展上。多年未見程先生,聽聞其退休后在北京等地居住。平日里,程小琪愛寫寫畫畫,日常繁重的工作確是全國某大報的資深傳媒人。他平日里愛穿著西服,白襯衣或吊帶褲,為人風(fēng)趣而幽默,儒雅又博學(xué),儼然一位年輕小伙子般,走路帶風(fēng),又爽又颯。長達(dá)10余年未見,仍記憶深刻,只因程小琪的學(xué)識。他所談?wù)摦嬍樊嬚摦嬋耍⒎墙炭茣纤姡墙Y(jié)合自身創(chuàng)作及理論與實(shí)踐。“橫看成嶺側(cè)成峰”用于畫藝論道上恰如其分。時而津津樂道,時而開懷盡興,我們印象極為深刻。當(dāng)時不認(rèn)同的觀點(diǎn),若干年后偶有想起,突然間覺得是對的。
許先生和程先生都愛畫荷花,都屬羊,都重情重義。“小琪有心了,中秋前,特意訂制了兩個超大的餅。”許先生的話打斷了我無邊無際的記憶,將我的思緒從很遠(yuǎn)很遠(yuǎn)的地方拉回到現(xiàn)實(shí)。許先生用雙手比劃著大小,比他桌面上的洗筆陶瓷盆還要大。“一個餅給我,一個給林藍(lán)。”許先生補(bǔ)充道,禮輕情意重。林藍(lán)善花鳥畫,近10年來重點(diǎn)關(guān)注嶺南地區(qū)獨(dú)有的花鳥景致,圍繞重大時間節(jié)點(diǎn)而開展的主題創(chuàng)作,深受群眾喜愛。她繪荷,在用色和材料上別出心裁。粵人性格中多為生猛和淡定結(jié)合。盡管生猛和淡定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性,但在粵人身上卻完美融合。林藍(lán)用金箔紙創(chuàng)作國畫,以《詩經(jīng)》為切入口,既有思路和想法,又深情不乏歷史厚重。《詩經(jīng)》中提到荷花的有三篇,分別是《邶風(fēng)·簡兮》《鄭風(fēng)·山有扶蘇》和《陳風(fēng)·澤陂》。《邶風(fēng)·簡兮》中,以花為意象,以“荷”喻美好的女子,如“山有榛,隰有苓。”中榛代表的就是男性,“苓”即“荷”,代表的就是女性。
林藍(lán)的荷花作品中線條疏密、曲直安排有致、有序、有度,黑白灰、明暗色調(diào)節(jié)奏的把握恰到好處。這些作品與作者早期習(xí)作,以水墨中國畫方式繪制的荷畫,就欣賞與品位角度而言,體驗感受是天壤之別的。近期荷畫中,其畫面語言無處不蘊(yùn)含著節(jié)奏秩序等邏輯關(guān)系。構(gòu)圖中的黑色和色塊安排的節(jié)奏,造型當(dāng)中的曲直方圓節(jié)奏,畫面中的虛實(shí),運(yùn)筆和色層當(dāng)中的厚薄與明暗、光亮與陰影等其他畫語言的節(jié)奏關(guān)系。林藍(lán)對于節(jié)奏感的把控精準(zhǔn)敏銳且穩(wěn)固,運(yùn)籌帷幄又不留痕跡。觀者能感受到作者用筆的松動狀態(tài),酣暢淋漓,筆觸長短厚薄不一,線與面的節(jié)奏默契優(yōu)美,單一的焦點(diǎn)透視構(gòu)圖,毛筆之下的散點(diǎn)透視。西方傳統(tǒng)畫的形體中,從古希臘開始,并沒有完全按照現(xiàn)實(shí)中真實(shí)的樣式去塑造。在古希臘時期,人們追求他們心中的一種樣式:完美的數(shù)字比例。畫家將數(shù)字比例引用在雕刻與壁畫當(dāng)中的時候,作品與真實(shí)的世界有了很大的距離。古希臘人用這些數(shù)字比例規(guī)定統(tǒng)一了所有作品細(xì)節(jié),形成完美的,具有抽象分割意義的一種美的追求。同理,以《詩經(jīng)》為創(chuàng)作靈感的荷畫,它們系作者心中自定義的“數(shù)字比例”應(yīng)用在畫布的映照,是作者在構(gòu)圖形體追求差異化而帶來的節(jié)奏韻律變化。
許先生說,程先生送的碩大餅,市面上少見,只有提前訂做。而近幾十年來,因需求少,商家供應(yīng)少,懂行會做的藝人也少。“我聽說最近大餅又興起了。拜神專用,頗受歡迎,一餅難求。”許先生如此與時俱進(jìn),天天在畫室,外面的世界,仍了如指掌。潮汕人內(nèi)斂儒雅,潮菜精細(xì)講究。餅深受喜愛,究竟贏在何處?一種食物能否立足并流傳,味道是關(guān)鍵。制作者、手藝人、傳承人、繼承者……稱呼可以無數(shù)個,適合當(dāng)?shù)厝说目谖叮蚴峭醯馈E品唤稚系纳啼仯u的點(diǎn)心,其實(shí)是餅的“兄弟姐妹”,它們與餅一樣,從未花心思在包裝盒宣傳上。程先生送出兩個餅給倆人,打包帶走的餅,更多的是給美加地區(qū)的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餅外觀為金黃酥皮,有些“脫皮”,歪歪斜斜的一個紅印的小餅,路人甲乙丙丁在牌坊街上打“蛇餅”,商鋪舊式的木門一扇一扇地被打開,街坊情緒高漲。排隊等待的過程,將情緒延遲,將興致推向高潮。一個貌不其揚(yáng)的小餅,牽動天底下多少游子的思念。改革開放初期,餅生意極好。街坊、親戚之間走動的伴手禮,游子出門前老母親的一汪眼淚:“細(xì)呀,路上餓了,吃哦。”母子連心,兒女走到天涯海角,長到滿頭銀發(fā),在母親眼里,仍是娃。餅的生意好,好到還曾是大宗的出口商品,遠(yuǎn)銷香港和東南亞各地。入口即化的餅,濃在心里,融在深情。
唐朝詩人王建有詩云:“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千古文豪蘇東坡曰,“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仲秋,月亮和食物多為圓的。天上的月亮是圓的,茶幾上的餅是圓的,互道的祝福是求圓滿的。月圓是天道,餅是世俗,祝福是人道,天地人自成一體。《易經(jīng)·泰卦》中有句“無往不復(fù)”。這四個字佐證了天地人三者間的“同道”:“圓”。追求圓滿,幸福而美滿,和諧而圓融,古人早已參透且著書立說。又大又圓的月亮,成了人世間的幸福團(tuán)圓的符號化標(biāo)志。羨慕或遺憾,求而不得或隨遇而安,多元而多態(tài),為中秋佳節(jié)增添了詩意、詩性和詩興。許固令、程小琪、林藍(lán),雖世代不同,確不約而同地喜愛畫荷花。他們雖不能變形成西子湖里的一朵荷花,但用手中的毛筆,畫出了他們內(nèi)心的荷花。他們在“荷”風(fēng)中暢游,在微醺中盡享“荷”風(fēng)拂面,這是前世的約定,也是未來已來的承諾。荷畫中,造型元素和造型結(jié)構(gòu)多元化,大小、形狀、方向,較有節(jié)制地變化。這不是簡單的重復(fù)或疏密,正負(fù)空間的交錯關(guān)系相當(dāng)復(fù)雜,視覺的秩序感最弱、無序且混亂,是有運(yùn)動感的獨(dú)特的視覺特征感受。這種感受猶如指尖上的芭蕾,天人合一,隨心所欲。為了常年持續(xù)保持手指的靈活和敏銳,許固令每天堅持彈鋼琴,畫紙和布面不過是鍵盤上的黑白鍵。毛筆撩動布面,畫紙留下戲痕。為了保持手指和手腕的靈活性,程小琪的八段錦,林藍(lán)的手指健美操,倆人總是見縫插針地“練手”。
荷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特質(zhì),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中,深植于藝術(shù)家和民間,成為古代詩詞歌賦中不可或缺的意象符號。早在《詩經(jīng)·陳風(fēng)·澤陂》中就有“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的詩句,這里的荷花便寓意著美好的人和事物,是對美好向往和惋惜之情的生動表達(dá)。屈原在《離騷》中寫道:“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荷花在此處成為了詩人高潔情操的象征,他以荷花為衣,象征自身清廉高潔,不愿同流合污的志向。
當(dāng)下的新時代文化思潮中,運(yùn)用中西方繪畫語言的共識,對于傳統(tǒng)優(yōu)秀中華文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性表達(dá)迫在眉睫。畫家們擁有一顆洞幽察微真誠遼闊的心,創(chuàng)新滋養(yǎng)心靈的繪畫藝術(shù)世界,或創(chuàng)造出一個又一個自由、浪漫、清新,令人喜悅而親切的藝術(shù)新境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深遠(yuǎn)的象征意義與美學(xué)價值。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郭洵汐
審核|詹樹鴻
- 李強(qiáng)簽署國務(wù)院令 公布《國務(wù)院關(guān)于修改〈全國年節(jié)及紀(jì)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
- 重磅!住房交易稅收新政來了!
- “進(jìn)度條”刷新!粵東城際鐵路潮州段首榀箱梁成功架設(shè)
- 聚焦“百千萬工程”| 潮安區(qū)萬峰林場望京坪村:黨群合力齊上陣 繪就鄉(xiāng)村新圖景
- 守護(hù)“打工人”健康!職業(yè)健康知識宣傳走進(jìn)潮安區(qū)鳳塘鎮(zhèn)盛戶村
- 【潮州】利好來了!電動自行車以舊換新補(bǔ)貼條件大幅放寬!
- 探尋潮州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新密碼”!潮州文化大學(xué)堂“品‘潮’尋蹤”第七期活動舉行
- 全國考核優(yōu)秀等次!為潮州的他們,點(diǎn)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