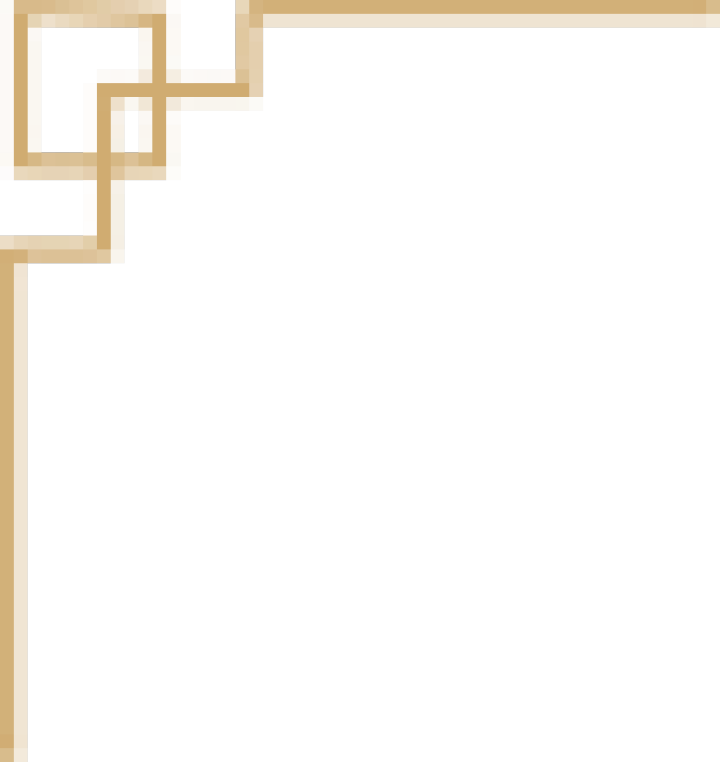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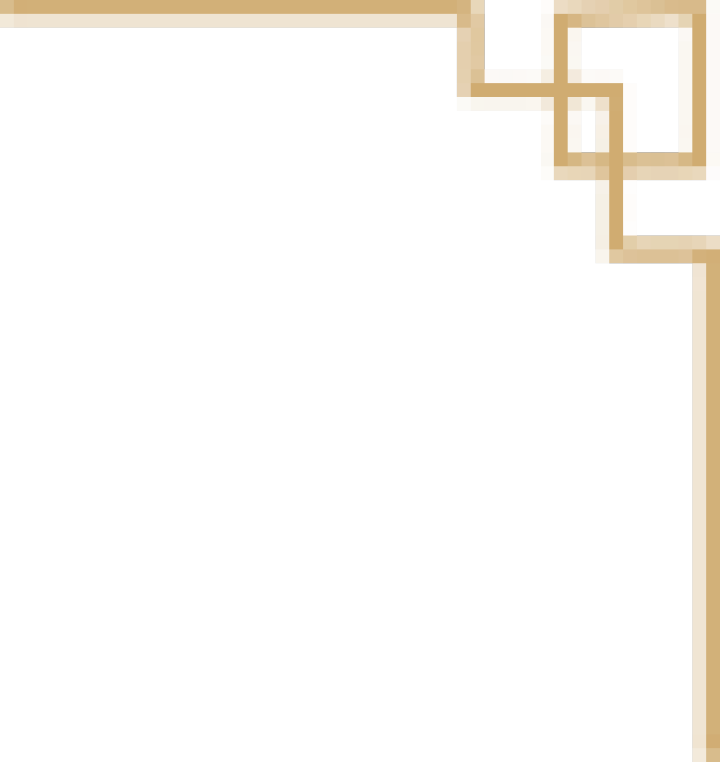
自是千秋虔俎豆 應知多士慶彈冠
——鳳凰洲奎閣史略
□?陳賢武
科舉考試從制度上打破了尊卑貴賤的界限,在封建社會中后期逐漸鑿出了一條正常而狹窄的社會流動通道。自唐宋以來,科舉已成為寒士躋身官場、獵取爵位、施展抱負的最重要途徑。“非是途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明·艾南英《前歷試卷自敘》)科舉考試帶來的科舉功名是讀書人獲得特權的制度保障。民間有諺語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對這一社會現象的形象描述。“凡于科試,即預士流。”(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即或沒有獲得正式科名者,由于參加考試進入科舉的征途就意味著擁有了獵取功名富貴的可能性,所以只要參加了這場科名的爭奪,也就享有一定的“特權”,還可以澤及家人。而對于獲得進士功名的讀書人來說,其人生前途更是無比光明,社會上也就出現了對科名無比崇拜的現象。

鳳凰洲奎閣
早在宋太宗朝后期,就已“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云”(《宋史·梁顥傳》)的科舉盛況,考取進士難度之大簡直難以想象!即使學問再好的舉子也無法把握自己在科場上的命運,因此,他們在皓首窮經的同時也需要寄托于神靈來“平靜”長時間備考、應考下的心態,緩解過于激烈的競爭帶來的壓力。隨著科舉考試制度越來越健全,考試環節也越來越多,只要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可能“滿盤皆輸”而與科舉及第失之交臂,諸多不確定因素也大大拓展了科舉迷信的市場,這是其社會歷史原因。
文昌帝君是道教尊奉的神靈。文昌星是文運的象征,原本是星官名稱,它不是一顆星,而是由六星組成,形如半月,位于北斗魁星前,因與北斗魁星同為主宰科甲文運的大吉星,所以常被人們與文曲星混為一體。其信仰與蜀中梓潼神張亞子有關,被道教吸收后,被尊奉為主宰功名祿位的星君,因迎合了讀書人求取功名的愿望,所以廣受尊崇,流傳廣泛。元仁宗時加封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明代開始在學宮建文昌祠,有祭神儀規。明代中期名臣王鏊說:“文昌,先天之孔子也;孔子,后天之文昌也”,“大有功于儒教”。(《文昌孝經跋》)清代嘉慶六年(1801),將文昌列入國家祀典的群祀層級,下詔稱“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祐民,崇正教,辟邪說,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關圣大帝相同,允宜列入祀典。”(《清朝續文獻通考·群祀考》)咸豐六年(1856),由“群祀”升為“中祀”,朝廷頒發文昌樂章、祝文,形成與孔子等同的局面。自都城以及各府州縣,莫不建祠崇奉,用意在于振揚文教、扶植綱常,故時人說,“文昌之祠遍天下”(清·朱鶴齡《新修文昌閣記》)。
在潮州,也同樣情況,在乾隆《潮州府志·祀典》對府屬各縣有記載:
海陽:文昌閣,一在縣學后,一在韓山,一在湖山,一在鳳凰洲,一在龍溪都大鑒洲,一在東莆都金石宮,一在上莆都彩塘市,一在登隆都塘東鄉。
潮陽:文昌閣,萬歷三十三年乙巳知縣王訓建,為縣署儒學之障,上祀梓潼帝君,春秋二仲致祭。下為諸生會課之所。有祠租,旁豎碑記。兩旁號舍三重二十一間。因颶風,閣毀。梓潼神像移祀鄉賢祠。寇亂不戒于火,碑碣悉焚無存。康熙十三年甲寅,知縣張宏美倡建,因亂中止。(光緒《潮陽縣志·壇廟》:康熙“三十年知縣臧憲祖就舊址鼎建。”“文昌廟,一在紫云巖。”)
饒平:文昌祠,在縣治東門內。文昌閣,在儒學前。
大埔:文昌祠,在學宮前左,明萬歷三十年壬寅,知縣王演疇、孝廉吳墀捐建。國朝康熙四十年辛巳,知縣周際春重修。貢生饒華袞倡建奎星樓。
澄海:文昌祠,一在冠隴神山之麓,因遷斥廢。(康熙《澄海縣志·祠祀》作創建于明崇禎七年。)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知縣章兆曾捐建。一在程洋岡丹砂寺,一在蓬洲鷗汀,一在南洋中社。
普寧:文昌閣,舊在城東之昆山,明崇正(禎)間知縣楊大行建。后毀。國朝康熙六十年辛丑,知縣羅秉琦,紳士方聲亮、方憲韶等捐建于城隍廟左。文昌祠,在培風塔下。
豐順:文昌閣,在北門外安敦嶺麓,距城一里,總鎮吳六奇建。
未列入的,在《縣志》也有相應的記錄:
光緒《揭陽縣志·建置志》:
奎閣樓,在文廟之左,巋然杰構,道光十二年創建。
雍正《惠來縣志·學校》:
文昌祠,在縣南郊外前。甲申火災。康熙二十六年,知縣張秉政以舊時坐向未吉,今改坐癸向丁,丙子丙午分金,后扆五朝,前面瀛海雙峰在右,云塔在左。祀文昌、魁星二神。春秋二丁設祭于此。門屋一座,后堂一座,左右二廊,為義學講習之處。
光緒《海陽縣志·建置略四》對《府志》則有所補充:
文昌祠,一在湖山,一在東莆都金石宮,一在上莆都彩塘市,一在登榮都山洋鄉,一在登隆都塘東鄉,一在東廂都涸溪堤,一在秋溪都新埠,皆各都講睦會文之所。
奎閣,一在縣學,一在府學,一在考院,一在道署,一在南門城角頭,一在韓山,一在鳳凰臺,一在龍溪都大鑒洲,皆兼祀文昌。又案:縣學、韓山奎閣,今俱圮。
“南門城角頭”的奎閣即潮州內八景之一“奎閣騰輝”。歲月無聲,當年海陽縣留存下來的只有官塘鎮北溪娘祠大橋旁、沙溪鎮寶云寺之文昌祠及鳳凰洲上的奎閣。
光緒《海陽縣志·古跡略一》:“鳳洲奎閣,即文昌閣,在城東南。康熙三十四年(1695),巡道魯超建。后圮。雍正七年(1728),巡道樓儼、劉運鮒,知府胡恂,知縣張士連重建。嘉道間遞有修改。同治間毀于火。光緒二十三年(1897),巡道聯元倡紳建復。二十七年春又毀于火。”聯元《鳳凰洲奎閣記》:“潮郡倚金山為城,鳳水縈繞之,城東曰韓山,西曰西湖山。東南地勢較低,是為鳳水之洲。其上有巍然崛立者,曰奎星閣,康熙三十四年巡道魯超建也。志稱:自建此閣,人文乃盛。”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一:“鳳凰臺,在鱷溪下流,當城之巽方(東南方),蓋江中一洲也。好事者構杰閣,以奉文昌神。”考是書為撰者于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使粵時所記,則在萬歷年間閣已存在,而不是清康熙年間方創建。先賢林熙春《修鳳皇臺兼建文昌閣募緣疏文》有:“前臺仍舊,復三十載之弘規;后閣維新,開千萬年之景運。祀從魁斗,意主文明。非壯麗無以重觀,茍卑陋安能致遠。是用掄瑰材(選擇珍奇的棟梁材)而僝梓匠(齊集木工與匠人),運心上之經綸(抱負與才干);憫農事而食子來(民心歸附),建潮東之保障。上棟下宇,重檐列自云間;直檻橫欄,干栱疊于日下。”康熙《潮州府志·人物列傳》說他居鄉“倡建鳳凰臺、三元塔,修玉簡塔”,考林熙春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因忠諫被貶,遂告病離職返鄉。二塔分別成于萬歷三十五年、萬歷三十九年,《粵劍編》所說“好事者”無疑即林熙春了。此外,庵埠大鑒洲文昌閣也是其所倡建,有《大鑒洲文昌閣募緣敘》《文昌閣上梁疏文》《請陸太尊文昌閣落成》等文章。
閣的風貌,清·林大川《韓江記》卷四有描述:“文閣,三層。……屹然獨立,為一郡之文峰。潮之科名,自此日盛。閣外邱步瓊書‘詩天酒地’。下層祀呂仙,聯云:‘一片婆心,要提醒世人,莫爭蟲蟻是非,釀成惡渚;三更劍氣,偶遨游海上,來看魚龍變化,飛過仙橋。’杜龍章、劉于山二人合撰。中層祀文昌、關帝,峨眉張熙宇題‘經文緯武’,聯曰:‘允文允武;乃圣乃神’,此系古聯,移來恰好。上層魁星,金山張中陽題‘文耀麗天’四字,聯云:‘彩筆昔曾干氣象;文章新人有光輝。’集句也。”
閣屢建屢毀,因是磚木結構,除受臺風、洪水影響外,更在于香火旺盛之緣故。“雍正七年重建,庚戌捷南宮(八年中進士)者十人”,而一旦被毀,則“都人士以為人材之衰,蓋由于此。理或然也。”使地方長官不得不順應民意,主持重建。(聯元《鳳凰洲奎閣記》)1999年,潮州市在原“鳳凰時雨”舊址修建鳳凰洲公園,奎閣得于重建,按照《韓江記》所載予以修復,重現聳閣三層,八面攢尖寶頂,典雅古樸,峻凌飄逸,巍峨壯觀的名勝建筑。一樓供奉五“文昌”之一純陽帝君呂洞賓;在二樓供奉有文昌帝君及文衡帝君關云長;三樓供奉的是魁星星君,作為賜科試第一的神靈,被人們尊為文運之神。魁星點斗瑞應圖和讀書人信奉魁星的風俗早在宋代就已出現,在明、清時期大為流行。俗就“魁”字取象,造為鬼舉足而起斗之像,立于鰲頭之上,一只手捧斗,另一只手執筆,一只腳向后翹起如大彎鉤,其相貌如宋代徐元杰《魁星贊》中形容:“頭發蓬松,形骸卓縮。瞋目怒眉,拈手弄腳。會看一踢北斗翻,恁時與我露頭角”,寓意魁星點斗、獨占鰲頭,寄寓著人們通過科舉成名,升遷晉爵的企盼。

《合修鳳凰臺文閣暨重建郡明倫堂兩廡碑》殘碑拓片
今存奎閣內壁的清乾隆二十年(1755)《合修鳳凰臺文閣暨重建郡明倫堂兩廡碑》殘碑中有“勝地作人,惓惓不倦,都人士弦誦興思,文品益懋,不徒婆娑簸珠,景趙子(趙德)之風行”,藉此祝奎閣長存人間,潮州文運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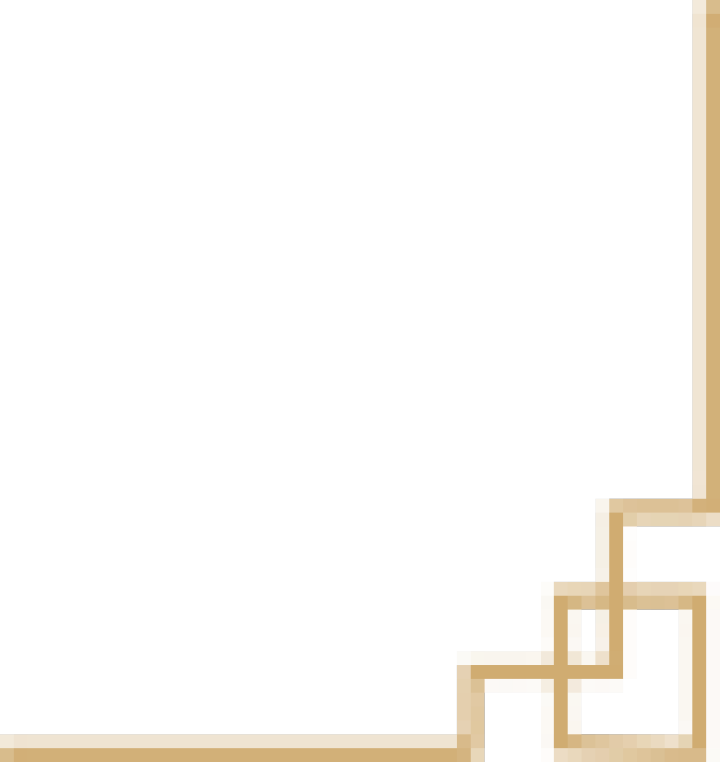
編輯|張澤慧
審核|龐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