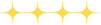
夜幕低垂,月色如水,銀輝灑落在故鄉(xiāng)的青石小巷。微風(fēng)輕拂,帶著春夜的涼爽。倚坐在斑駁的門(mén)檻上,抬頭忽然瞄見(jiàn)掛在墻上那把陪伴父親多年的樂(lè)器——冇弦,我油然想起那空靈悠揚(yáng)的潮州音樂(lè)旋律,想起那段溫馨而難忘的鄉(xiāng)居生活。
父親是個(gè)地地道道的鄉(xiāng)下農(nóng)民,但他的一生都與冇弦緊密相連。小時(shí)候,我常常看到父親農(nóng)閑時(shí),端坐在那張破舊的竹椅上,將冇弦椰殼琴筒置于左腿上(有時(shí)是夾在兩腿中間),左手持琴五指按弦,右手執(zhí)馬尾弓夾于兩弦間拉奏,一張一弛,樂(lè)聲便抑揚(yáng)頓挫彌漫整個(gè)屋子。那時(shí)的我,總是好奇地湊上前去,想要一探究竟。父親總是笑著摸摸我的頭,說(shuō):“等你長(zhǎng)大了,就教你鋸冇弦。”
冇弦也叫嗡弦,規(guī)范的樂(lè)器名應(yīng)該叫椰胡。潮州話(huà)的“鋸冇弦”其實(shí)就是拉椰胡。別小覷這把看似普通的冇弦,在父親的手中卻煥發(fā)出了不一樣的光彩。它的音箱是用海南椰子殼做成的,弦桿上裝飾著貝殼,弦碼則是由蚌殼制成。每當(dāng)父親拉起它,那獨(dú)特的音色便如同海浪般涌動(dòng),仿佛帶著我一起穿越,回到那片遼闊的原野。
我記得父親平時(shí)最喜歡自?shī)首詷?lè)的曲目除了《平沙落雁》《出水蓮》《素閣》《寒鴉戲水》《將軍令》《柳青娘》《拾杯酒》《大八板》外,還有《春月明》《昭君怨》《哭皇天》《拋網(wǎng)捕魚(yú)》等傳統(tǒng)潮州音樂(lè),紅色經(jīng)典作品《珊瑚頌》隨想曲、阿炳的《二泉映月》也是他的至愛(ài)。這些樂(lè)曲旋律優(yōu)美,音韻蕩漾,扣人心扉。那時(shí)對(duì)于不懂音樂(lè)的我,只覺(jué)得父親親手制作的冇弦很漂亮,奏出的聲音美輪美奐如天籟之音,令我百聽(tīng)不厭。
父親說(shuō),潮州音樂(lè)中稱(chēng)為“冇弦”的椰胡,又稱(chēng)小胡,形似板胡,音色渾厚,地方風(fēng)味濃郁,通常用以合奏或伴奏,是黎族、漢族弓拉弦鳴樂(lè)器,流行于海南、福建、廣東一帶。音箱用椰子殼制作,面蒙薄桐木板,背開(kāi)5個(gè)出音孔,用小貝殼(或竹)做弦碼。他還說(shuō),音樂(lè)沒(méi)有貴賤之分。冇弦是貧苦大眾的朋友,也是高雅音樂(lè)的靈魂。無(wú)論是在田間地頭,還是在書(shū)齋雅室,都能發(fā)揮出它獨(dú)特的音樂(lè)魅力。有錢(qián)人可以用高貴的螺殼來(lái)裝飾它,而農(nóng)民兄弟也可以用“簡(jiǎn)裝”的椰殼來(lái)抒發(fā)內(nèi)心的情感。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也逐漸長(zhǎng)大。讀大二時(shí)我開(kāi)始學(xué)習(xí)“鋸冇弦”,從生疏到熟練,每一個(gè)進(jìn)步都離不開(kāi)父親的悉心教導(dǎo)。父親總是耐心地糾正我拉弦的錯(cuò)誤,告訴我如何掌握節(jié)奏和力度。他說(shuō):“鋸弦不僅僅是對(duì)樂(lè)器操作技巧的掌握,更應(yīng)該是對(duì)每一首樂(lè)曲的理解和感悟。”
在父親的影響下,我漸漸愛(ài)上了潮州音樂(lè)。每當(dāng)心情低落時(shí),我便會(huì)拿起那把冇弦,輕輕撩撥,讓樂(lè)聲撫慰我的心靈。冇弦仿佛成了我的知己,它懂得我的喜怒哀樂(lè),也陪伴我見(jiàn)證了前進(jìn)路上的許多風(fēng)雨彩虹。
然而,歲月不饒人。父親終究抵擋不住時(shí)間的侵蝕,1992年春夏之交他病倒了。在病榻上,他依然念念不忘那把陪伴他多年的冇弦。我?guī)追l(fā)現(xiàn)他眼角閃爍著期待的光芒,想要再次拿起那把冇弦,奏響他那熟悉的潮樂(lè)旋律。
在父親生命的最后時(shí)刻,我拿起那把冇弦,坐在他的床邊,輕輕地?fù)軇?dòng)琴弦,讓《寒鴉戲水》《出水蓮》等潮州音樂(lè)裊裊之音在房間里回蕩。聽(tīng)著,聽(tīng)著,父親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他仿佛又回到了自己以前農(nóng)閑自?shī)首詷?lè)的時(shí)刻……
如今,父親已經(jīng)離開(kāi)我多年,但他那把冇弦依然陪伴在我的身邊。每當(dāng)我拿起它,我都會(huì)想起父親那慈祥的笑容和深沉的眼神。
在這個(gè)喧囂的世界里,冇弦拉響的樂(lè)聲仿佛是一股清流,它洗滌著我的心靈,讓我感受到溫暖和寧?kù)o。我會(huì)繼承父親的遺志,走好人生每一步,用它“鋸”出華麗的樂(lè)章。
父親的冇弦,是一把充滿(mǎn)故事和情感的樂(lè)器,它將永遠(yuǎn)陪伴著我,成為永恒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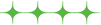
作者 |?謝岳雄
編輯 | 翁純
審核 | 詹樹(shù)鴻
- 李強(qiáng)簽署國(guó)務(wù)院令 公布《國(guó)務(wù)院關(guān)于修改〈全國(guó)年節(jié)及紀(jì)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
- 重磅!住房交易稅收新政來(lái)了!
- “進(jìn)度條”刷新!粵東城際鐵路潮州段首榀箱梁成功架設(shè)
- 聚焦“百千萬(wàn)工程”| 潮安區(qū)萬(wàn)峰林場(chǎng)望京坪村:黨群合力齊上陣 繪就鄉(xiāng)村新圖景
- 守護(hù)“打工人”健康!職業(yè)健康知識(shí)宣傳走進(jìn)潮安區(qū)鳳塘鎮(zhèn)盛戶(hù)村
- 【潮州】利好來(lái)了!電動(dòng)自行車(chē)以舊換新補(bǔ)貼條件大幅放寬!
- 探尋潮州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新密碼”!潮州文化大學(xué)堂“品‘潮’尋蹤”第七期活動(dòng)舉行
- 全國(guó)考核優(yōu)秀等次!為潮州的他們,點(diǎn)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