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味小說《打春》:
百窯村和她的一千年
□?潘子揚
5月,青年作家張淳的新書《打春(完整版)》由羊城晚報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以粵港澳大灣區千年商貿史為題材,展現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嶺南風”,用長篇小說的形式演繹《廣東通志》之北宋社會經濟史。作為并不多見的帶史學注解的長篇小說,書的封面和內頁設計采用小說所寫歷史時期的宋銅錢、廣州宋代西村窯瓷器、潮州北宋百窯村瓷器、宋代海船指南魚等作為設計元素,以抽象化的航路彩帶圖形象征“海上絲綢之路”,別具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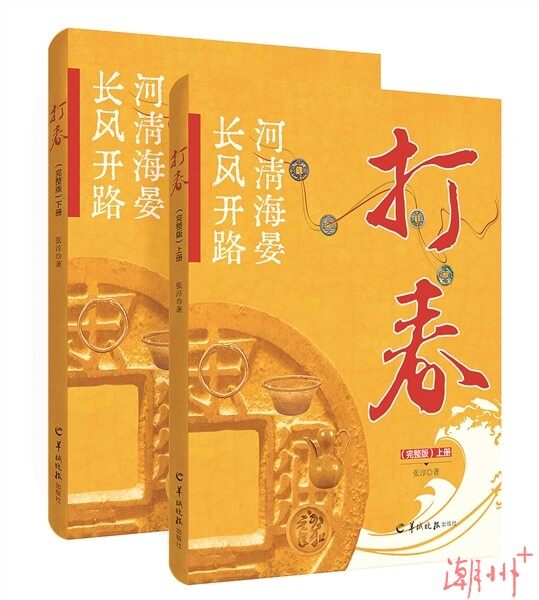
百窯村和“陶瓷之路”
《打春(完整版)》是一個關于百窯村的故事,女主人公從百窯村走出來,最后又回到百窯村。百窯村的興盛又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密切相關。北宋前期,潮州港是粵東的重要港口。宋代韓江流域是瓷器生產中心。韓江東岸的筆架山號為“百窯村”,瓷器主要供給出口。潮州港及附屬于它的鳳嶺港使粵東一帶的物產,特別是韓江流域的陶瓷可以直接出海,成為廣州港的良好補充。據1985年出版的《廣東唐宋窯址出土陶瓷》:“外銷方面據記載,當時在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國的首府縛達城,已有不少經營潮州陶瓷的商販。”
莊義青先生在《宋代潮州陶瓷生產及外銷綜述》一文中稱,在潮州出土的陶瓷器皿和裝燒爐具上面,可以看到一些有意刻劃的符號和文字。例如在許多匣缽的外壁上刻著“蔡、李、五、六、十、廿、陳、朱、丫、川”等。一些研究者推斷說,這些字和號反映的是當年潮州陶瓷業的生產關系概況,瓷窯的所有制是一種合作股份制。這種推斷有一定道理,可能基本符合歷史實際。
宋代潮州瓷窯基本都是民窯,屬民間自主經營。潮州的陶瓷業是在外貿需求的刺激下,在較短的時期內蓬勃發展起來的。靠的是本地豐富的瓷土原料、燃料,方便的河道運輸和港口轉運,產品成本相對較低。潮州城周圍數以百計的窯灶,大部分屬于個體窯戶所有。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生產資料所有者,有的全家人都參加此項生產勞動。
這種以個體窯戶為主的生產關系上馬較易,費用較省,成本較低。這種個體小窯戶必須走合股經營、聯合燒制的道路。因為改進了的龍窯容量很大,一般長度都在二三十米以上,有的長近百米,有必要合股燒制、經營,以達到充分利用爐容,節省燃料,降低成本的目的。筆架山古窯群,是宋代潮州古瓷窯的核心部分,其外圍部分包括潮州城南郊、西郊、北郊、澄海蓮下程洋岡等處。
小說中,初試瓷器經營的女主人公沈阿契還與廣州西村窯試制端硯的瓷硯版,為做好蜜望果營銷,燒制精美又易于保存果子的瓷魚瓶。西村窯是廣州宋瓷的典型代表。據【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西村窯是廣南東路產量大、質量高的瓷窯,在國外及地處中國至南海諸國航道上的西沙群島海域都有不少發現。
小說中有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情節,就是“壓軸戲”云龍窯的出場,重要成因之一就是沈阿契傾囊買下飛鳳嶺瓷土礦,為瓷藝大師崔響提供了上好原料。而沈阿契之所以能獨具慧眼,正是因為盧彥曾經的指點迷津——瓷土多產于溫泉附近。原來,長石類由于溫泉或含有碳酸氣的水、沼地氣體起作用,常能發生變質形成瓷土。
粵商和蕃商,民生視角的“北宋夢華”
“頭家(老板)”“頭家阿娘(老板娘)”等嶺南方言的植入,使《打春(完整版)》中的粵商(該書主角是潮商)有了新面孔。小說展示了嶺南文化的核心價值與主流價值,如重商崇商之氛圍、務實開拓之精神、博大通融之胸襟、仁愛正義之人文等。除了粵商的塑造,書中更有對從諸蕃國來宋貿易的古代蕃商形象的描繪,帶入別具一格的異域風情。
作者在寫粵商形象時選擇從平民視角切入,意不在濃墨重彩于極盡神化的豪商巨賈,而用素描的方式寫出淡去光環,也沒有三頭六臂的普通人。他們弱小,所以他們在生產經營中摸索出古人早期的股份制經營方式,將許多股細繩擰成一股粗繩,既應用于瓷窯,也應用于遠洋海運。他們是“頭家”,同時也可能是全家男女卷起褲腿就露出兩腳泥的生產者。“打春”作為奮斗的代名詞,并沒有將奮斗理想化。我們耳畔響起的仿佛還是云龍窯追求精品時一次次砸爛成品的碎瓷聲。
嶺南荔枝在該小說中也不僅僅是一種水果,它是海上貿易“臺柱”,還催生了期貨貿易雛形。這樣的嶺南荔枝是否顛覆了你對荔枝的認知?宋人用“紅鹽法”加工荔枝,可經久保存,解決了遠洋運輸的問題。宋代商人買賣鮮果荔枝還采用了類似期貨的方式,“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后豐寡,商人知之”。(見宋人筆記《荔枝譜》)作為外貿“臺柱”的荔枝,成為嶺南支柱產業之一。但這些關于荔枝的說法,并非純粹小說之戲說,宋人筆記早有記載。
小說中嶺南地區的不少宋人宋事是從《廣東通志》中走出來的。宋代的嶺南佳果柑橘、蘋婆果都曾為貢品,而奇花異木蓊蓊郁郁更是嶺南景象,也有了嶺南奇花綱的故事。《廣東通志》記載,太平興國三年,知廣州李符獻《嶺表花木圖》,又有“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煩擾,轉運使黃震奏罷之。”顛覆今人認知的更有宋代潮州的野象活動。
經濟史角度的小說
《打春》是一本經濟史角度的小說,不僅有“錢荒”和解決“錢荒”的故事主線,還有作為北宋金融一條街的“界身巷”;細民交易的城郊貨攤“草市”;有質押場所“解庫”、匯款機構“便錢務”;有糖霜、染料等產業的戲劇性演繹,也提到作為納稅品的平紋綢、作為納稅中介的“攬戶”;有不動產交易的“投稅請契”,也有宋代女性參加契約活動能否成為“契首”等經濟地位的探討。
例如,作為“國際貨幣”的宋銅錢。“錢荒”和解決“錢荒”是貫穿了大半部《打春(完整版)》的一對戲劇沖突。由此折射的不僅僅是一個“內部”現象。在宋代,中國海船與紅海沿岸、非洲東海岸都進行了直接貿易,與60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非洲盛產象牙、香料,都是中國市場暢銷的大宗商品。非洲也發現了大量的宋瓷和宋錢。張方平《樂全集》卷二六《論錢禁銅法事》有載“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之。”據【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及【日】桑原騭藏《蒲壽庚考》,東亞、東南亞、南亞、阿拉伯、非洲等地均有宋銅錢出土發現,如北宋的“淳化元寶”,可見宋代銅錢流布之廣。
潮學泰斗杜經國、黃挺在《潮汕地區古代海上對外貿易》中記載,廣東澄海隆都后埔宋代佛寺遺址曾出土宋銅錢1800多斤,當時佛寺前是出海港,佛寺則是海商集會之所。這些銅錢是蕃舶收買而因故未能啟運的走私品。這成了小說中反派錢匪“陸銅錢”的一個原型出處。
小說還講述了海上絲綢之路推動北宋經濟新現象的兩個事件:一個是香藥交引的問世,一個是占城稻的引進。
北宋前期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是出口大宗,香藥是進口大宗。最初,所有的香藥寶貨都綱運進京,在批發環節進行“官營”,后來隨著進出口體量的不斷增大,舊的運輸模式出現了成本倒掛,催生了香藥交引,從而減輕了綱運成本的壓力。包括香藥交引在內的有價證券被應用于社會面,解決實際問題,被視為宋代金融的一次進步。
同樣應運而生的是占城稻的引進。起初,不同地區在經濟產業鏈上有著默契的分工,海上貿易的開放打破了原來不同路之間的供需平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宋代海商從購進占城米,到引種占城稻,推動了當時農業科技的進步。據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70頁),占城稻最初由海商販運至福建、潮州等地,潮州尤其繁育出白占、黃占、赤占等許多品種。


編輯|郭洵汐
審核|吳燕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