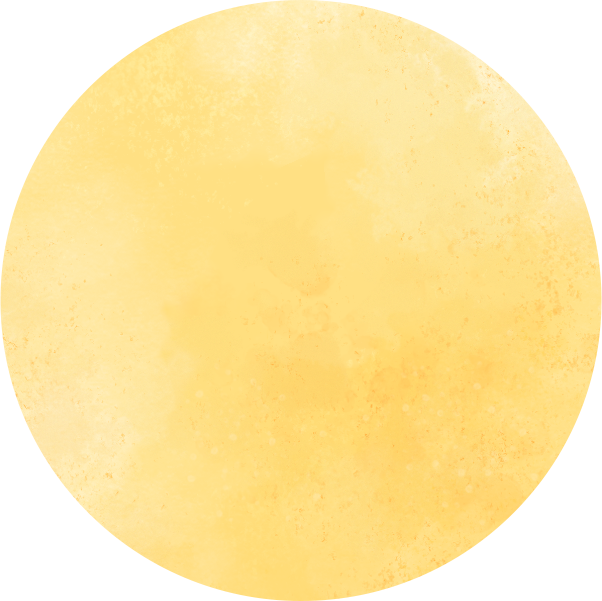
潮州人的中秋節
□ 陳樹彬
“云蓋中秋月,雨淋元宵燈。”
潮州一句俗語,生動描述了傳統節日的習俗,又形象凸顯了季節特征。

中秋節,不管華夏大地習俗有幾多差別異同,在這一天的夜晚,總會“存異求同”,寄托共同美好愿景。這其中少不了“賞月”。
每逢中秋,“拜月娘”、吃芋頭和“燒瓦窯”是潮州人過節的重頭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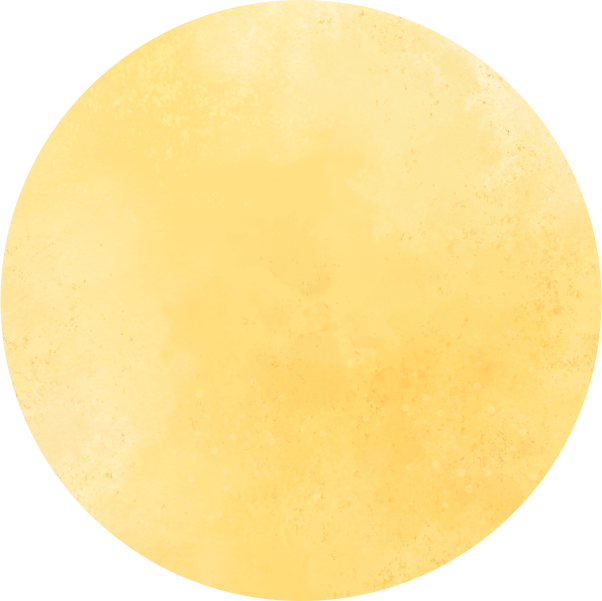

潮州人中秋夜拜月,俗稱“拜月娘”。“月娘”是哪位神仙?小時候童蒙未開,懵懵懂懂,反正大人讓跪拜祈禱,就有樣學樣跪拜禱告。后來讀書識字,知道了嫦娥奔月的神話故事,就認定“月娘”就是嫦娥姐姐。大人對小孩子稱嫦娥為“姐姐”很是介意。嫦娥是神仙,是月娘,怎么能稱“姐姐”呢?亂了禮數,有褻瀆神明之嫌,是大不敬。當然,在大人面前,小孩子不敢違拗,跟著大人恭恭敬敬稱“月娘”,背地里,幾個毛頭毛腦的孩子依然大大咧咧叫“嫦娥姐姐”。奇怪,也沒見得“月娘”怪罪。

“月娘”還是月娘,孩子卻一茬一茬長大。長大后的孩子,從別處得來了一種大人所沒有的“知識”:“月娘”居然不是嫦娥姐姐。是一位叫“太陰娘娘”的神仙。因為嫦娥奔月之前,月宮早已有“主”,就是“太陰娘娘”,是道教神話人物中的月神。這說法,好像欽定的,太陰娘娘就是月宮的宮主,是撼不動的名正言順的“月娘”。然而,不僅長大后的孩子不這么認為,連大人們都執意認定嫦娥就是“月娘”,拜“月娘”就是拜嫦娥。
太陰娘娘在民間的知名度遠遠不及長袖善舞、美麗不可方物的嫦娥姐姐。
“嫦娥奔月”的故事影響深遠,就算陰差陽錯,觀念依然根深蒂固!
有關系嗎?民間祭祀,不外某種人力不可為而寄托于神明的善良愿望、莊重儀式。何況,嫦娥在所有人心目中,就是美麗和善良的化身。

在潮州人“拜月”的供品中,除了毫無爭議的月餅、水果等,最讓外地人不解的是,大人們還會用大大的紅盤子,擺放上筆記本、筆等學習用品。不單外地人不解,孩子們更疑惑。其他傳統節日的拜神儀式上,從沒見過擺放孩子們的學習用品的。這是哪門子“創意”呢?不解歸不解,迷惑歸迷惑,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做到了,便有“自圓其說”的理由。這時候,大人會說:“月娘不是喜歡小孩子嗎?這不可以保佑你們小孩子平平安安,學習進步嗎?”
答案,就這么簡單!
簡單到我們怎么想都想不到!
然而,當答案昭然揭開了,又不得不從心底里信服,并由衷佩服這種有如“神助”的創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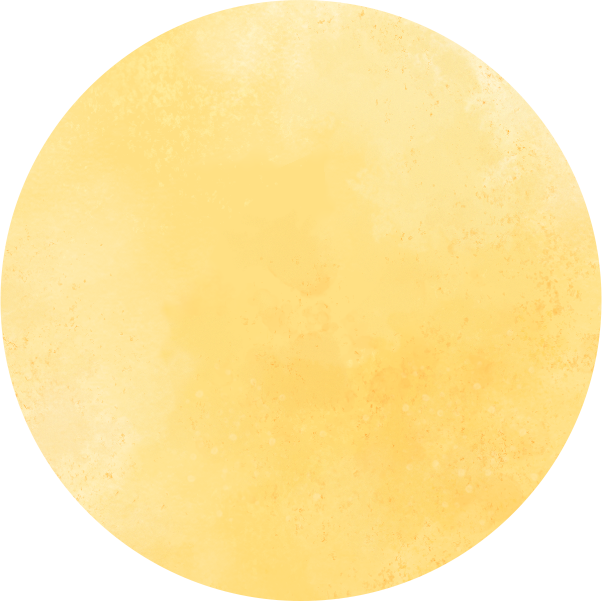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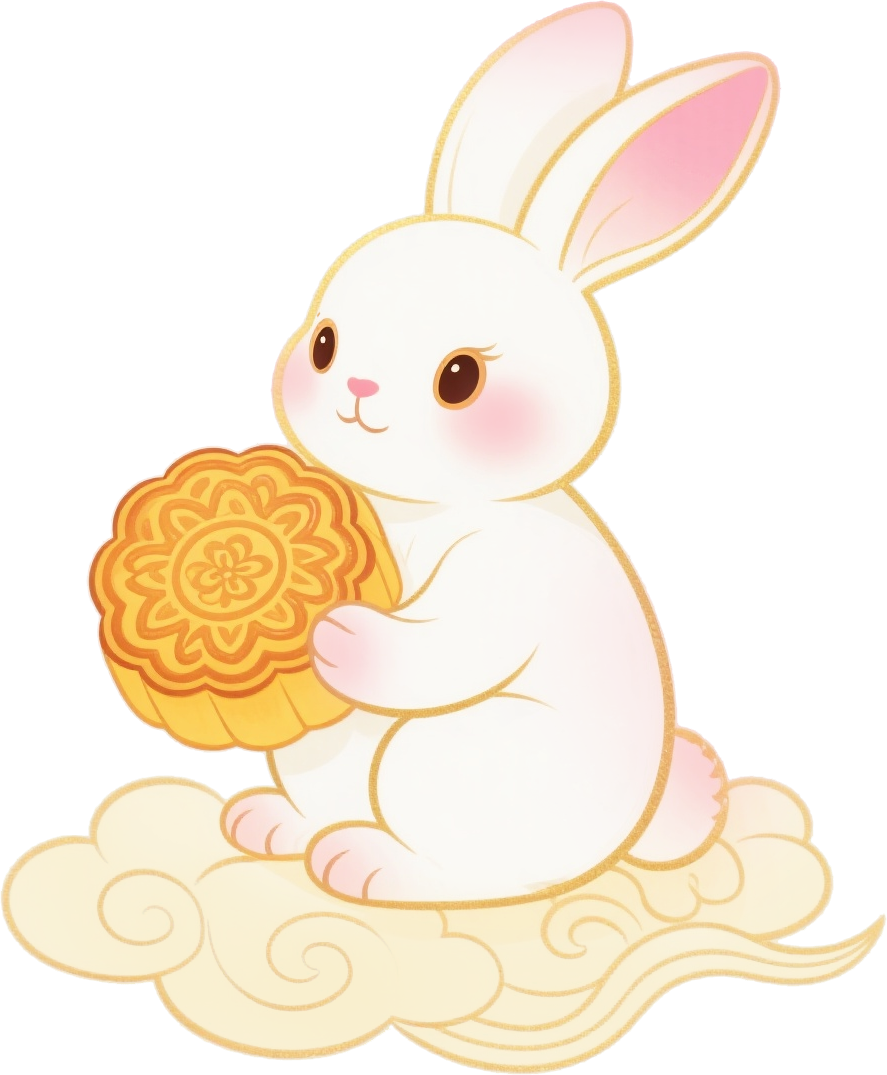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民間習俗,自有源頭可溯。這源頭,有“恨”,更多的是“愛”。民間習俗,在科技、文明不如今天昌明隆盛的年代,其源頭,往往寄托著人們對世道人心中揚善懲惡的希冀。

幾乎每個習俗都有著一個揚善懲惡、鼓舞人心的傳奇故事,口口相傳,不斷完善,沿襲下來,甚至可以編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傳奇電影。
中秋節,潮州人有吃芋頭的習俗,寄辟邪消災寓意。清乾隆《潮州府志》載:“中秋玩月,剝芋頭食之,謂之剝鬼皮。”民間有關中秋食芋頭的寓意,則是另一個愛恨情仇的傳奇故事:南宋末年,元兵入侵潮州,攻進潮州城后,實行聯戶制(三家一保)。也就是每三家人供養一個元兵吃、喝、拉、撒、睡。甚至有的元兵喜歡想睡哪家的媳婦賴哪家床上。如此無賴、下作,下流、無恥,百姓對元兵恨之入骨,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對于敵兵的恨,便假借某種不易覺察的隱蔽方式表達出來。蒙古兵,過去被稱為“胡人”。而“胡”與“芋”潮州話是諧音。人們便把對“胡人”的恨,假借“芋頭”加以發泄——砍“胡”頭,剝“胡”皮,食“胡”肉。這是初露端倪的覺醒。從覺醒到反抗,不過是時間問題,這中間,等待的是時機,是人心的團結。后來,同仇敵愾、忍無可忍的老百姓終于奮起反抗了。他們把約定起義時間寫在紙條上,置于月餅中,并以燒瓦窯為信號在中秋之夜起義。
后來,起義成功了沒,好像沒有后續故事。反正,沒有民族認同感、在歷史長河中聲名并不佳的元朝支撐不了多久,就讓四處揭竿而起的義軍干掉了。
潮州人關于抗元的民間故事,實實在在為我們“貢獻”了中秋之夜燒瓦窯的獨特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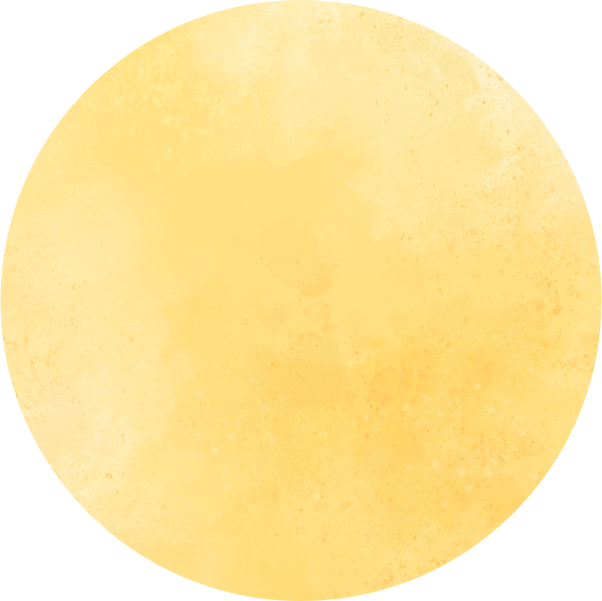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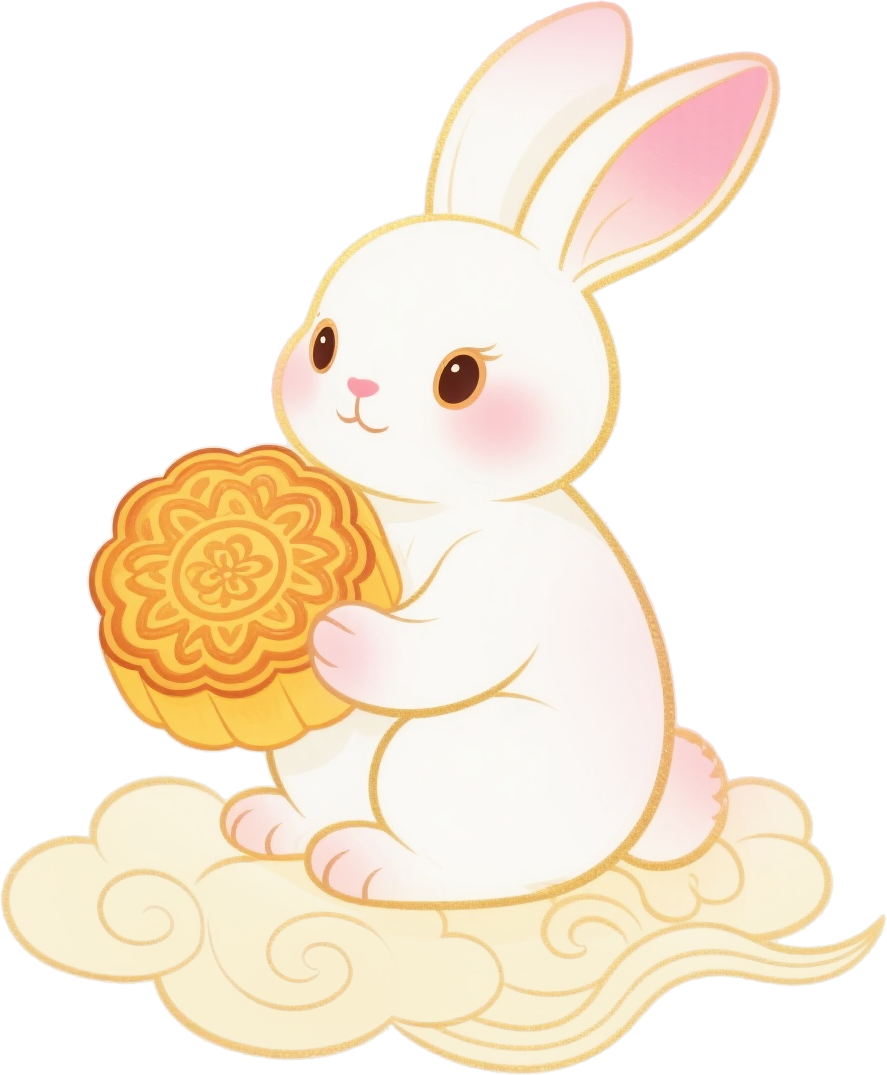
中秋夜,燒瓦窯,過去村村有。
燒瓦窯的習俗,甚至比“拜月”更為隆重。“拜月”雖然家家戶戶都有,自有獨特的“儀式感”,但僅限于較小范圍的私人空間,是“獨樂樂”的個體活動。燒瓦窯是舉一村之力的集體活動,是團結和諧的“眾樂樂”。

現在的“瓦窯”,其實是“磚窯”,是用磚塊砌起來的,一般有四五米高,矗立在壙埕上,高大威猛,威風凜凜。燒起火來,氣焰高漲,更是熱烈壯觀,氣勢磅礴!
過去的“瓦窯”就顯得瘦小單薄了,不僅沒顯出高大威猛,甚至“相貌”也不見得多挺拔俊逸。
但,卻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換的“瓦窯”。
首先,“瓦窯”是由貨真價實的瓦片砌起來的。
我很奇怪“瓦窯”為什么不叫“瓦塔”。不管大小高矮,它看起來就是“塔”。而且,叫“瓦塔”不是更威風,更響亮,更吸引眼球?
何況,擺在(而不是矗立)壙埕的是一個不外兩米高的瓦窯,你把它吹成“塔”,只會徒增笑話,人們卻不領情的!
現在,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叫“窯”而不是“塔”。
如果你年紀大了點,在那個沒有電腦、手機的年代,參加過當年“砌瓦窯”的活動,見識過當年燒瓦窯的場面,就更能理解“瓦窯”不可能砌成“瓦塔”。
“砌瓦窯”是一項融集體智慧和集體勞動的“工程”,不是現在有了錢就能分秒解決的事情。
中秋節前的一個月,全村的孩子會自發在村子前后,每個角落,每個旮旯地帶撿瓦片。這些瓦片,大大小小,大多殘缺不全,是村里人建房子殘留下來的。那些日子,見到瓦片就像撿到寶一樣。
那個時候,沒規定誰有“撿瓦片”的義務,但,都約定俗成似的。人人覺得有這個推卸不了的義務,責無旁貸!而且,誰撿的多,誰就特別自豪。這種自豪,來自于一種人人皆有的集體榮譽感。

中秋節的上午,幾個領頭的大人就圍攏起來開始砌“瓦窯”。沒有固定的,但幾乎每年砌“瓦窯”的都是那幾個大人,大概都已經有了經驗,重要的是骨子里那份熱情、那個熱心。當然,也有臨時加進來幫忙的大人。之后,便集聚了越來越多的小孩子。小孩子是打下手的,不是遞送瓦片,就是瞪大眼睛緊緊盯著,怕瓦窯會因什么意外倒塌似的。
大人先是找來幾個涂角。長方形體的涂角,用于建房子砌墻體的。過去,我們這里建房子砌墻體,不用磚塊,用涂角。涂角,是用灰砂土與貝灰作為原料,填進長方形模子夯實而成。
幾個涂角圍起來當成“瓦窯”的底座,再用幾條磚塊架在上面,接下來,再層層疊加瓦片。有了涂角和磚塊“打底”,瓦窯才顯得牢固。
疊加瓦片也是有講究的。每疊上一層平面瓦片,就要加上一層U型瓦片,交叉疊加,這樣,既提高效率,又使瓦窯通風透氣,有利于燒火。每疊加一層,瓦片都要稍微靠里邊挪,才能使瓦窯的“口”慢慢收攏,最后自然形成“塔尖”。
砌“瓦窯”的大人當然是師傅級的。這個無師自通,靠的是“目色”,就是目力,看得準,還得膽大心細。稍微擺放不當,失去平衡點,“瓦窯”就會坍塌,前功盡廢,成了“豆腐渣”工程。一切從頭再來,費時費事,坍塌的不僅是“瓦窯”,還有在別人心目中的“威望”。
砌“瓦窯”的“師傅”,都會把這當成“面子工程”,關乎面子!
這也算是“工匠精神”了!
砌好的瓦窯,便等待著晚飯后熱烈而隆重的活動。但瓦窯不孤單,總有一撥又一撥的參觀者接踵而來,欣賞、品評。
晚飯后,趁著拜月前的空當,進行燒瓦窯最后一項準備工作——派草。
派草,就是一群孩子,分幾撥挨家挨戶攤派干稻草。或抱著,或抬著奔走著來到壙埕,堆放在瓦窯旁邊。仿佛約定俗成的,每家每戶早就準備好了一大捆干稻草,放在家門口。“派草”的小孩子來到家門口,吆喝了一聲:“派草嘍!”然后扛起干稻草就飛奔而去,那個興奮勁,不亞于參加奧運會比賽!
晚飯后,家家戶戶在門口擺上桌子,開始“拜月”。“燒瓦窯”也會趁著當兒隆重開始。
所以,當大人催著孩子“拜月”時,會給個“溫馨提醒”:還不快點,燒瓦窯開始了!孩子趕緊跟著大人跪下,合十禱告時,大人還在旁邊面授機宜:“保號,保號,保號阿奴棒棒大,讀書讀強強,將來做宰相……”沒講完,孩子早起身開溜,屁顛屁顛跑到壙埕看“燒瓦窯”了。
燒瓦窯持續的時間多久,要看燃料的量。負責燒瓦窯的會把握節奏,既不能讓瓦窯斷火、熄火,又不能燒得太快。保持瓦窯自始至終火勢持續,過程越長越好,中間偶爾來幾下“小高潮”。負責燒火的會把一根長長的竹竿伸進瓦窯的入口,把燃燒的干稻草有節奏地往上撩撥,這一撩撥,火勢更猛更旺,紅彤彤的火舌伸出瓦窯的縫隙,整個瓦窯就像一座烈火焚身的“火塔”。這時候,孩子們就會蹦著跳著,拍手歡呼。老人們告訴過孩子們,這瓦窯燒的,就跟過日子一個意思:紅紅火火,興旺發達!
燒瓦窯的中間,“拜月”完畢的阿姨大媽趕著過來看下半場。當然,她們沒空著手來。她們從家里頭帶來了食鹽,把食鹽往熊熊燃燒的瓦窯一撒。烈火燒到了食鹽,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真正“有聲有色”,又把“燒瓦窯”掀起一個小高潮。
聽老輩人講,“燒瓦窯”還有一個寓意:潮州話的“瓦”,跟螞蟻的“蟻”讀音相同,“燒瓦窯”,就是把“螞蟻”燒個精光。夏天的螞蟻最為活躍,中秋節,借“燒瓦窯”消除螞蟻,特別是“白蟻”,還真是一舉多得。
又是讓人腦洞大開!
又是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創見”。
明月懸空,柔光如水,褪去熱烈后的柔順溫存,適合安安靜靜“賞月”。
這時間節點,喧嘩后的寧靜,真的適合仰望星空,與明月對話。
賞月的人,有著不同心思,卻有著相同情態。
如同今天,再也回不到那個青澀而純真年代的我們,共賞一輪明月,該會有著跟當年相同的情態。
多年以后,終于明白了。“月是故鄉明!”不僅僅是,故鄉的月有別于他鄉的月,更因了故鄉的明月曾經照亮并且見證了再也回不去的那些朦朧情景,以及那些朦朧的人和事。
當年,我們的許多愿景,大多今天如我們所愿實現了。但,再回首,我們是不是更懷念那個月光下許愿的羞澀而美好的面容,更懷念為實現這些愿景卓厲奮發的矯健身影,更懷念那些熔鑄著堅苦卓絕的汗水和熱血?
那是一個有著和如水月華一樣皎潔純凈的情懷的年代。
愿明月依舊,人依舊,情懷依舊!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郭洵汐
審核|梁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