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編輯師友 (之三)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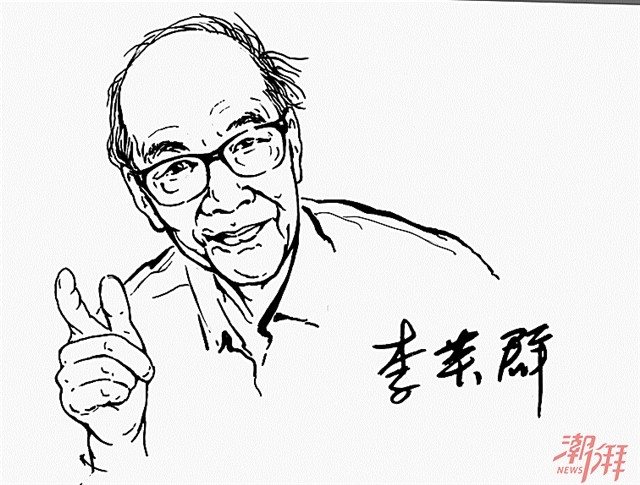
人們把作者與編輯的關系,比喻為產婦與接生婆,頗有意思。這可能出自編輯之口。嬰兒出生,稱為出世;作品發表,稱為面世。一聽就覺得是編輯老師的口吻。
是的,所有作品都經編輯之手而得以出世的。但有些編輯對作者及作品的盡心盡力程度,我認為接生二字不足以表達,應是催生。這種編輯應稱為催生婆。
白翎先生就是一位作品催生婆。
我手頭有一部白翎兄簽贈的他的散文集《這里的夜靜悄悄》,封底印著作者簡介:“白翎,原名李友忠,1931生于泰國曼谷,祖籍廣東潮安。童年在故鄉農村度過,二戰后返泰。1948年重回中國,就讀于潮安省立金山中學,并工作一段時間,1957年底返泰定居。先后在《新中原報》《亞洲日報》《京華中原報》執編文藝副刊,多次參加國際文學活動。現任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秘書。”
認識白翎先生,是1991年春在曼谷。當時,我隨同我所供職的潮劇團赴泰國訪問演出。剛抵曼谷,在機場大廳受到旅泰僑領的熱烈歡迎。一位記者上前來送給我一張名片,是我的高中同學范模士托他帶給我的。
范模士是我1955至1958年在潮安高級中學的同班同學,他的經歷與白翎頗相似,出生于曼谷,祖籍潮陽,回中國讀完高中,再返泰定居。業余喜歡文學,名片上印著“泰華作協理事”。
當時,隨同我們出訪的謝望新,是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作家。他很賞識泰華作協的司馬攻、夢莉等人的散文,很想能與他們見見面,讓我設法聯系。我把這想法告訴范模士。到曼谷一周后,我們應邀來到泰華作協辦公樓。
走進大廳,迎面辦公桌上赫然是一套潮州工夫茶具。幾位坐著的作家朋友都站起來迎接。范模士一一作了介紹:會長司馬攻,副會長夢莉,秘書白翎,還有幾位理事。
一坐下就沖起工夫茶,因為謝望新不是潮州人,聽不懂潮州話,談話就雜著普通話、潮州音以至潮州話。于我來說,這套工夫茶具就足夠驚奇了,來曼谷一周,總喝冰鎮飲料,今日見此茶具,似見老朋友。我說:都說卻認他鄉是故鄉,我看,一杯工夫茶,此處即故鄉!
坐在一旁的白翎先生眼睛發亮瞪著我說:“李先生,寫出來,把這感覺寫出來,給我!”
過后,他怕我爽約,還吩咐范模士提醒并催促我。對于他鄉似故鄉的感覺,一周的曼谷生活,我是有體會的。每次站在湄南河西岸向東望,對岸的鄭王寺總讓我想到在潮州東門樓前望東岸,見到韓文公祠。于是,從韓江連著湄南河的意象,寫了一篇《從韓江岸到湄南河畔》給了《新中原報》。
有一次與白翎先生閑聊,他深情地回憶他的金中生活。當時學校搬在開元寺,他最思念美術教員洪風老師。我告訴他:洪風老師的公子洪鐘這次也隨團前來,他是劇團舞美設計師。白翎立即要求見面。洪鐘應約前來,手里正好拿著一疊相片,從洗印店剛取出來,他是個攝影家。
見面之后,邊聊天邊看相片。我見其中一幅是河岸一臨水吊腳樓,洪鐘是從河里游船向岸上拍的;正面是樓的一個陽臺,敞開向著河面。有一對老人在小凳上閑坐,七八十歲樣子,一看就是一對夫婦,很從容、閑適地望著河上風景。那敞開的陽臺像極了一個戲臺。我說:一個舞臺,二人世界。有多少活劇在這里上演,現在到了最后一幕了。
白翎奪過相片看后說:好,詩配畫,英群兄你配詩,就是《一座舞臺,二人世界》!
我沒拒絕,在他們的聊天聲中,完成了十幾行詩。三天后,這詩配畫出現在《新中原報》文藝副刊上。
我的老同學范模士,在泰華文壇上被稱為鬼才,他不單小說散文很了得,也寫相聲,方言詩。他的小說構思奇特,故事性強,人物形象鮮明,作品很受讀者喜歡。夢莉說他多次說他學創作是高中時受我影響,這讓我也沾了光。
在泰國逗留近兩月,與泰華文友多次聚會。臨走前,有一件趣事:范模士有一篇小說,寫一位媒婆的機智,她教一位新娘子洞房之夜如何配合丈夫,化解尷尬,渡過難關。后又有幾個關口,她都從容應對,左右逢源,處處逢兇化吉,又處處有錢賺。二千字寫活四個人物,難得的佳作。但卻受到遠在廣州暨南大學一位青年教師的批評,撰文稱此小說低俗、黃色。泰華作家們很不以為然,范模士顯然有點生氣。我則覺得這位評論者認為寫房事即低俗,即黃色。人家合法夫妻的行為有何可責,更何況并沒具體寫性事。
白翎絕對同意我的觀點,讓我盡快寫出來。于是,臨離開曼谷,我又被他催生了一胎。
范模士和幾位泰華作家都覺得我的文章很解渴,在《新中原報》發表后,他們寄給與泰華作協交往密切的暨大副校長饒芃子教授。
旅泰近兩月,公務之余,我竟被催生了六、七胎,胎胎順產。
白翎先生,你這位文壇催生婆,罕有!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