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何喜愛潮劇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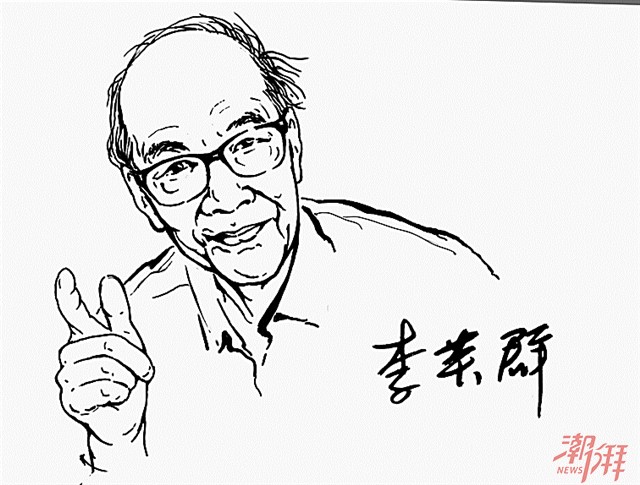
這是一串很有意思的答問。因為不是新聞記者進行采訪那么認真嚴正的問和答,是茶座中隨意的對談,回答都非常實際,語言也非常本色。
下面記錄的答話,隱去真名,只提供性別、年齡、職業。
問題只有一個:你為何喜歡潮劇?
甲(女,中年媒體人):我小時候陪祖母去看潮劇,看到那些演員穿著戲服,戴著頭盔,尤其是鳳冠,很美麗,十分羨慕,就想將來當個演員,打扮得漂漂亮亮在舞臺上亮相。
這樣就開始爭取去看戲,就被吸引了,不再只喜歡服裝之美,更有劇情的動人,唱腔之迷人等。
家內人不支持我考戲,我大學畢業后投身媒體當上文化記者,重點就在采訪潮劇的編導、演員。在潮劇界有了不少朋友。
乙(女,中學教員):我現在是個潮劇迷。我喜歡潮劇,是從迷戀它優美的、雅俗共賞的唱詞開始。
我是個中學語文教員,課文中有一些古詩詞,選的都是經典名篇,都是文言文,學生初接觸別說不感動,連理解都費力,只能逐句逐字解釋。而我去看潮劇演出,那唱詞一聽就入耳入心,能懂能品味,就叫雅俗共賞吧。比如蘇六娘中,六娘母親唱詞"我明知兒比蓮子心更苦,怎知母比青梅淚更酸”很易懂,很文雅。這種句式也是一種創新,很有特色。
再比如《井邊會》中李三娘咬指寫血書,那兩句“數盡飛鴻書不至,井臺積淚待君看"我一聽就直拍腳腿。
我有一本精美筆記本,專門摘錄潮劇精彩唱詞。當然,戲看多了,我明白潮劇之妙遠不止唱詞,那音樂,那唱腔,都令人百聽不厭。
丙(男,企業財會人員):我寫了不少文章評論潮劇藝術,大多談演員的表演。從外面看,我是個熱愛潮劇的人。當然,現在說我喜歡劇,我不否認。
但我最初有意接觸潮劇,是悅著一位花旦演員。當時,我還是個大學生,被朋友拉去看潮州戲,一個小花旦,俊俏靈巧,唱聲清麗,長相極符合我的審美標準,一下給迷住了,就希望認識她,變成朋友。我毫無門路可接近她,羨慕記者可去采訪,忽然靈機一動,覺得可以寫藝術評論這條路。我還算機靈,先評論該團一位老生演員,他是副團長,評論他以后認識他,就可由他牽線認識小花旦。
我的評論發表后,我帶報紙上門拜訪那位老生,當然受到熱情接待,稱我為老師,沖茶伺候。我就說那小花旦的表演也值得寫文章。老生立即把花旦叫來,接受我的訪問。這就認識了,文章也寫成見報了,送報上門也受到熱情歡迎。但過后數次約她出來吃個點心談談心,總被謝絕,人家一點感覺也沒有,我也不再追求,倒是對潮劇藝術越來越有興趣。
丁(男,演員,已轉行開茶葉小店):老丑呾白話,我去當演員,不是出于對潮劇的喜愛,而是覺得當演員易出名。我從小就想長大當名人,覺得做戲很易出名。你看洪妙、姚璇秋、張長城、李有存,他們文化都不高,小學都沒畢業,但知名度遠超各市的大領導。為出名,我投身從事潮劇。因為我長相好,嗓子也好,進劇團時信心滿滿。但進到劇團當學員,很快就感受到當演員的苦,每天早早起來練聲,叫吊嗓子,咿咿呀呀,每天練那一句曲,那二句口白,練身段,踢腿壓腿,壓得一個星期無法蹲下大便。看那些已能出臺的哥哥姐姐們,我看已演得很好,卻并不出名。李老師,你說過百年出個姚璇秋,千年也難出個洪妙,這我相信。勉強在劇團混了三年,演過幾個配角,無法出名,就主動辭職了。
我出來后,卻懷念劇團來,覺得生活中不能少了潮劇,所以,現在我是曲社的骨干,與票友們一起樂著。
離開劇團,更愛潮劇。
戊(男,壯年農民):我愛潮劇,是覺得潮劇很有趣味。做奴仔時,正月頭村里“營老爺”,有大鑼鼓隊,隊中有化妝游行,最好看是《楊子良討親》,厝邊阿叔扮乳娘,學洪妙行路,過好笑。當年村里有個業余劇團,我常去當個茶童,有時大人不在,就跟小伙伴學做戲,演《桃花過渡》,我扮渡伯,"囈了囈"一陣,過過戲癮。
近年來,潮州城鄉到處辦曲社,我們村的曲社辦得有聲有色,市里的老師們常常下來輔導,他們說我的唱曲水平排尾,對潮曲的熱心排在頭。我說:是,我總是包頭包尾。
其實,我唱《寶蓮燈》中劉彥昌那段《十五年前登此峰》還是不錯的。現在票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女的,男的很少,所以我受歡迎,她們與我合演《包公會李后》《柴房會》..
我現在每晚都應邀到各家曲社去唱,一唱就精神十足,就通身爽快,這是很好的運動啊,現在肚飽,再不尋巧,再不運動,你看這個肚,不唱就突出來……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