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雨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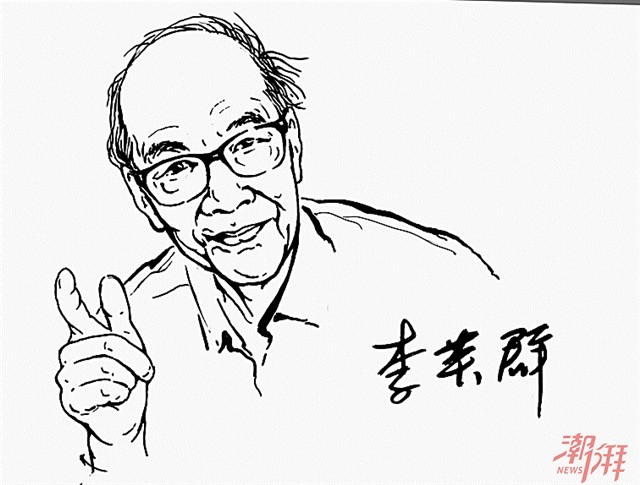
汪曾祺先生有篇小散文《昆明的雨》,被他收入他的許多選本,我手頭這本剛收到的《人生忽如寄》也收入了,足見人們喜歡的程度。
其實,《昆明的雨》主要是寫昆明雨季時各種植物的旺盛生長,真正寫雨就只有“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并不使人氣悶。氣壓不低,人很舒服。”
雖是寥寥數語,既寫出特點,也寫了人的感受,這就足夠了。
中國文人,寫雨的詩文,浩如煙海,面對各種雨,喜的悲的愛的怨的樂的苦的,抒盡了人的七情六欲。其實,都是人在自作多情,與雨一點無關,它仍然該下就下,該停就停,才不管你深情淺情。杜甫就有“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春夜喜雨;也有茅屋為秋風所破后“雨腳如麻未斷絕"的秋夜惱雨。
汪曾祺在文章結尾寫了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這我相信,不然,他就不會在離開昆明40年后寫下這篇文章。
對于我來說,我也想念雨,卻不是某時某地的雨,而是所有我經歷過的雨,包括暴雨,是不是有點怪?
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雨的隨想》,很簡單地寫鄉下人與城內人對雨的截然不同的態度:鄉下人是見雨來了,發出“雨落落,阿公去柵萡”的歡唱,城內人則發出“落雨了,猛猛收衫、關窗”的驚叫!
其實,這篇短文我只寫了一個情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潮的文學界領軍人物曾慶雍大哥,在家鄉當農民時,旱天車水灌田的故事:一年春旱,眼看稻田龜裂,禾苗半黃,老慶兄感到自己也口渴難忍,日夜到田中車水。這天挑著水車出門,有人提醒他:南肚浮烏云,雨欲來了。是的,南方天邊有大幅烏云。民諺云:南肚浮烏云,草粿賣有存。這是九成九下雨的征兆。但老慶兄仍不放心,怕是“旱天假雨意”,還是挑車前行。有雨點下來了,他仍不停步。終于嘩啦啦下起大陣雨了。老慶兄對我描述當年:把水車撂下,把竹笠脫下,坐在車上,任憑雨淋。真個是全身爽快!
我能體會,農民與莊稼是同呼吸的。我們潮州農村,種水稻為業。水田欲水,絕不嫌雨。所以,對雨有感情。我少年的歲月在鄉下度過,在野外經歷過各種各樣的雨,對雨有強烈的好感。
在離開農村到外謀生的歲月,我樂意于遇雨,觀雨,感受天賜甘霖。
曼谷的雨是豪爽的,干脆的,說下就下,說停即停。我第一次去曼谷,住在耀華力路的帝國飯店。漫步在耀華力街上,烈日炎炎,突然一片烏云從海面飄來,到你頭頂,噼里啪啦一陣豪雨從天而降,街上一陣騷動,大部分行人躲到騎樓下去避一避,少數人并不當回事,任憑雨淋。曼谷市民出門不帶雨傘,他們都穿單衣,為短袖上衣。一陣雨就都濕透。但雨很快就停了,幾分鐘的時間吧,猛烈的陽光又射下來,從湄南河吹來的一陣陣風,很快把濕了的上衣吹干了。
陳復禮先生的攝影自選集中選了一幅《喜雨》,就是拍我上文描寫的耀華力雨中街景:市民有人避雨,有人仍從容閑步。畫面正中是一騎三輪車工友,任憑豪雨掃著,笑得很開心。
新加坡的雨,比曼谷的豪氣有過之而無不及。新加坡人稱他們國家的氣候是“四季皆夏,一雨成秋。”他們也是正滿城陽光刺眼之時,一片烏云從印尼那邊越海飛來,突然變成噴水器,驟雨從天而降。市區多樹,那強烈的穿林打葉聲,增加雨的豪壯氣概。不過,沒見到市民像曼谷人一樣在雨中從容,他們的樓與樓間有許多封頂走廊連接。街上是雨的世界,望去極為壯觀。烏云很快離開市區,留下地上一片濕漉漉在陽光下空明耀眼。
我一直想寫一篇《雨落新加坡》,去了兩次,都未寫成,今日在此補上一筆,略盡余興。
此后,又有多次出境的機會,去過好多個國家,但都未遇到當地落雨,直到那次去圣彼得堡,才有幸又一次見到異國的雨。
這次的雨不是陣雨,是綿綿細雨,這天一早就開始下個不停,我們的活動項目是乘船游涅瓦河。
坐在雨中的船上,雖然沒有“白雨跳珠亂入船”,卻有水面空蒙雨也奇的意境。岸上的冬宮似披了薄紗,別有韻味,這就叫煙雨吧?
我們的船一直駛到涅瓦河出口芬蘭灣,這就是波羅的海了,在煙雨中,混沌一片,也不知藏著多少秘密。
雨是多姿多彩的,有機會,我想去看巴山夜雨,看天街小雨,看渭城朝雨,尤其是,冬季到臺北去看雨!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