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飽想巧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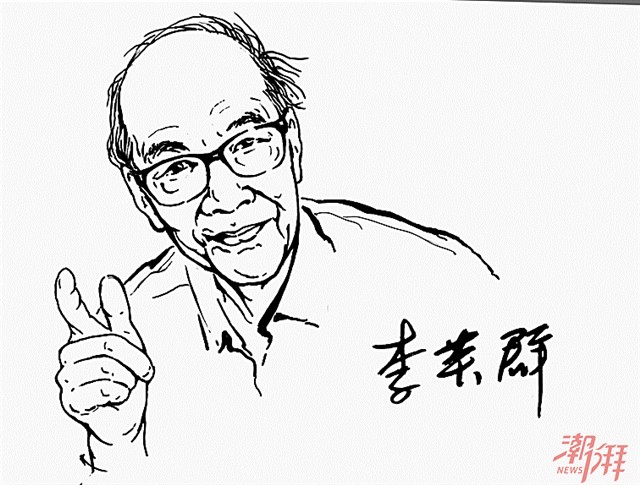
潮州俗語“肚飽想巧”,也有說“肚飽覓巧”。前者只是心理活動,后者進了一步,已是身體行動。
吃飽了肚子就想要巧,要尋巧。這“巧”是什么?
巧,是個形容詞。形容精細、靈敏、美麗(巧笑)等,也形容虛偽(巧言令色)及恰恰好(湊巧)之類,都是捉不到摸不著的一種感覺,想是可以的,但要覓卻無從下手。所以,我一直覺得潮州人有點令人難以理解。
我不理解,并不說明別人不理解,若真不理解,他們就不會無端創造這個短語,而且一直在使用。
直到約三十年前,有一次我到鄉下去采訪,順便拜訪我一位嫁到本村的老家鄉親大姐阿心。男主人引我進客廳,揚聲告訴其妻子說有客人。阿心姐聞聲從房里出來,手里還拿著剪刀和一張紅紙,男主人說她閑著無事在學剪紙。阿心姐笑著說:“肚食飽,無事覓巧。”說著揚了揚手中的紅紙。
我心中一怔:這就是我一直弄不明白的“巧”了!
我就故意問她剪紙作什么用?她說:無路用,剪趣味。
對了,她的所謂覓巧,就是尋找趣味。 此后,為了印證這一結論,我就注意觀察,也在一些適當的場合有意提示:讓同行人覓巧,即尋找趣味。比如那年三月,到濱江長廊去散步,木棉花掉了一地,同行的阿玲就跟她七、八歲的女兒,撿了木棉花,在地上擺了個心形圖案,整個過程都興致勃勃。完成之后,引得路過的一位畫家當場作了一幅圖。
這次濱江之行,趣味橫生。
一次,友人小丹約我到鄉下去欣賞田園風光,品嘗農家菜,她們姐妹二家,帶有4個小孩,到一處農家菜館,設在河邊。吃過飯,我們大人沖起工夫茶,小丹帶小孩在河灘上玩,開始是在打水漂,但河灘上都是鵝卵石,瓦片很少,我見小丹就帶孩子們在玩泥巴。這河岸近水處是粘土,濕度剛適合捏“涂安仔”(小泥人),他們玩了好久,似乎很投入,我過去看,只見他們捏了一套工夫茶具,頗精巧,心中有點感動:這就是他們肚飽之后覓到的巧了。這巧不是別的東西,完全是精神層面的趣味。
心想:我們出來旅游,不就是來覓巧么?覓巧,必須以肚飽為前提。我的青少年時代,在鄉下,根本不會有旅游這件事,有句俗語說:“看什么?看了莫非肚會飽?”
現在,旅游正在我國大熱著,我以為:旅游,是肚飽之后的大巧!
潮州人,肚飽之后,想巧覓巧,而我國有古語,在《增廣賢文》中就有“溫飽思淫欲”這樣的民間俗語,這令人覺得很不是滋味。當然,《增廣賢文》收錄這俗語,只是一種警示并非教示。但我由此則很為我潮這句“肚飽覓巧”而自豪。
從阿心姐的巧是剪紙,讓我認為潮州的許多名聞天下的工藝品,如木雕、潮繡、手拉壺以至大鑼鼓、英歌舞等等,都是潮州人肚飽之后想出來、覓出來的。
潮州人為何要作田如繡花?為何厝要皇宮起?潮州菜為何要在追求色味香上下大工夫,把一款款菜肴的造型弄得似小盆景般悅目?又為何要把上百種小食制作得像一件件精致的工藝品?這似乎都可以從“肚飽想巧”的俗語中找到答案。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