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編輯師友 (之三)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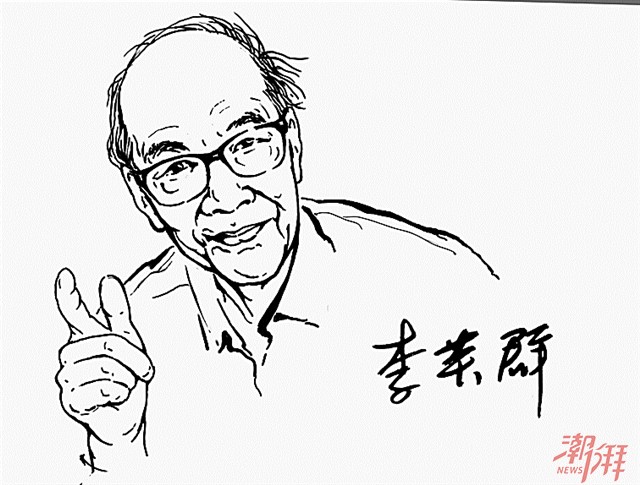
我是1956年開始向省里的報刊投稿的。那時,我從鄉(xiāng)下到府城來讀高中,學(xué)校的圖書館閱覽室訂了許多報刊,我對《南方日報》和《廣東僑報》的文藝副刊上的文章很喜歡,就試著寫一點自己的生活見聞投出去。
當(dāng)時,學(xué)校里發(fā)生一件新事:潮州醫(yī)院收到一位病人,急需輸血,庫存中沒合適血型,就向緊挨著醫(yī)院的我們學(xué)校求援。同學(xué)聞知,紛紛趕去醫(yī)院獻血。有一位血型合適的同學(xué)給病人獻了血。一個多月后,病人出院,專門到學(xué)校來感謝獻血者,提了一籃子雞蛋來。見面時,獻血同學(xué)見到的是一位臉色紅潤的少年,相見甚歡。
我如實記下這感人的一切,形成一篇近千字的短文《友誼》投給《南方日報》,在1956年12月3日發(fā)表了。這讓我很受鼓舞。寒假回鄉(xiāng)下老家,得知當(dāng)時為解決我們村的農(nóng)田一直為缺水所苦,政府全力興修水利。從府城北關(guān)筑一引水渠直達我們揭陽農(nóng)村,一道筑在田野上的引水渠,讓清清韓江水可以自流灌田。一位村里僑居泰國的番客回來探親,見此大為感動,眼含熱淚說如果早有這條浮溪,他也不用遠走南洋。我也為他所感動,寫了一篇千字文《老華僑的贊辭》寄給《廣東僑報》,被采用發(fā)表了。
1957年新創(chuàng)刊的《羊城晚報》的文藝副刊叫《花地》,辦得真叫精彩,尤其是對文學(xué)青年的扶持關(guān)愛令人印象良深。我把自己讀初中時,學(xué)校文藝演唱隊到一水庫工地去慰問,為農(nóng)民的勞動熱情感染下去參加勞動,又臨時創(chuàng)作新節(jié)目演出而大受歡迎的往事,寫成一篇叫《新節(jié)目》的小散文寄給《花地》,也被采用了。
這三篇小文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的小事。我一個高中生,沒有進行藝術(shù)加工,也不懂什么藝術(shù)加工。省里這些大報的編輯老師一點沒有嫌棄我的稚拙采用了。我明白他們意在培養(yǎng)新人,心中極為感激。此后就斷斷續(xù)續(xù)給這三家報紙投稿,至1965年的10年間,發(fā)了二十多篇小文章,但一直不知編輯老師是誰。
一個機緣使我不止知道了許多省里報刊的編輯老師,而且是直接聽取他們的耳提面命。這就是1965年底我被調(diào)到新成立的縣文藝宣傳隊任專職創(chuàng)作員以后的機遇。
當(dāng)時,中南局各省的每個縣,都成立一支15人的文藝輕騎隊,深入到工農(nóng)兵中去以文藝形式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這15人都是一專多能,歌舞、小戲、曲藝是主要形式。每到一個演出點,都要求有唱當(dāng)?shù)匮莓?dāng)?shù)氐墓?jié)目, 這就需要大量的曲藝作品可供演出。加上當(dāng)時各公社以至許多生產(chǎn)大隊都有業(yè)余文宣隊,也需要這類本子。于是,省文化廳常召集一些重點縣的文宣隊創(chuàng)作員到廣州集中創(chuàng)作,我也多次應(yīng)約赴廣州。在那里,我接觸到廣東文藝界許多名人,其中好些就是報刊的編輯老師。我這里介紹兩位對我?guī)椭艽蟮木庉嫛?/span>
我們在廣州創(chuàng)作的作品,被指導(dǎo)老師認可的,一般都推薦給演出單位演出和交給《農(nóng)村文化室》發(fā)表。
《農(nóng)村文化室》是省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曲藝雜志,跟我們這些作者聯(lián)系的是編輯王偉軒老師,一位極樸素極風(fēng)趣的廣州人,他很容易交往,對我們青年人很熱情,下班時請我們幾位作品稍多的作者到他家做客,彼此嘻嘻哈哈。我記得當(dāng)面向他表示感謝,還說以前投稿被采用卻不知編輯是誰,無從表示謝意。他說:你錯了,是編輯應(yīng)該感謝你們,你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沒有你們的供稿,巧婦如何作炊?我請你們來坐來喝茶,就是表示感謝!說實在,每次讀到一篇高質(zhì)量來稿,我比自己寫出來還開心!
我受感動了。創(chuàng)作會議結(jié)束,回到單位,我仍給他寄稿,有一首快板《石頭村》,我用心經(jīng)營,他在《農(nóng)村文化室》上發(fā)表了,后來還被編選入初中語文課本。你說這是我的成績,還是王老師的功勞?
給我的創(chuàng)作鼓勵最大的是黃雨老師,他是澄海人,著名詩人。我有他簽贈的古詩詞集《聽車樓集》,其詩風(fēng)直追杜甫。認識他時,他是《廣東文藝》的執(zhí)行編輯,他來過潮州,我還陪他到楓溪去采訪,我去廣州,常與文友李國俊被他約到家中共餐。
1976年,全國舉辦一次曲藝調(diào)演。我的一首潮州方言女聲彈唱《工地十姐妹》入選,演員們上北京我沒同行,黃雨老師把我約到他家,他說《工地十姐妹》已決定近期在《廣東文藝》上發(fā)表,并已入選他主編的《廣東曲藝選》,并把一本未加封面的樣書送我。我說這是潮州方言作品啊,行嗎?
他說就是要這潮州方言,能用方言寫得這么精彩很難得。
我知道,抗日戰(zhàn)爭時他流落香港,出版過潮州方言長詩,可惜我未讀到。我告訴他,我真的喜歡方言寫作,但郭光豹和雷鐸多次勸我用普通話,我沒聽。
他說用外地人可讀懂的方言,作品特色更鮮明,尤其寫詩,更有韻味。
我深受鼓舞,就說起我對口語俗語的入迷,舉例說“早田腳踏龍眼花,晚田腳踏龍眼皮”的農(nóng)諺,他不禁拍案說:這不比“鋤禾日當(dāng)午,汗滴禾下土”精彩嗎?!
記得那天這話題說了很多,他的意思是方言入文要提煉,又要保留原味,這需要下工夫。
我記住了,多年來都努力實踐著。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