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編輯師友 (之一)
□ 李英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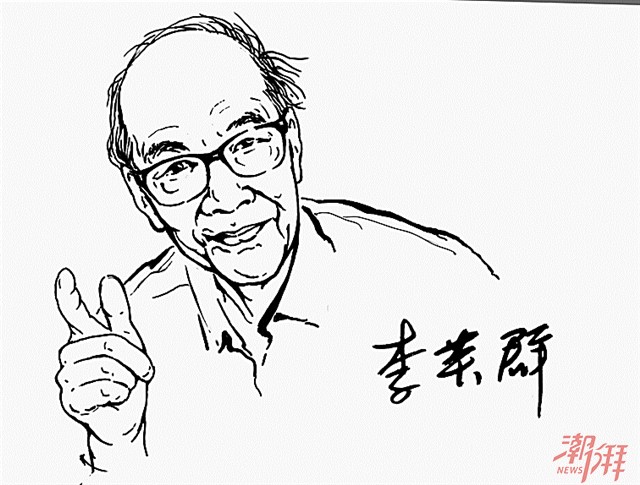
我是個寫作人,曾在專業(yè)藝術(shù)團(tuán)體當(dāng)過創(chuàng)作員,專門寫曲藝和劇本。業(yè)余,我則寫些短小的散文隨筆。我把這些散文隨筆投給報刊,為我審閱、修改潤色的編輯少說也有幾十位,這些編輯是我的老師,是我的朋友,多是亦師亦友,他們都是甘為他人作嫁衣的專家,無私奉獻(xiàn)著他們的才智,我對他們一直心存感激。
這些編輯師友,有的見過面,有的通過信,更多的是從未謀面,連姓甚名誰都一無所知、無從表示感謝。
我是1955年1月開始我的創(chuàng)作生涯的。第一篇稿子是小散文,投給《工農(nóng)兵》文藝月刊。
這篇稿子在三月號的《工農(nóng)兵》上發(fā)表了,負(fù)責(zé)修改、編發(fā)的編輯是夏濃老師。
我為何知道呢?因?yàn)槲亦l(xiāng)土改時,一些識字的翻身農(nóng)民在工作隊(duì)的幫助下,提起筆來歌頌新生活,在報刊上發(fā)表了。土改隊(duì)的同志就幫助鄉(xiāng)里成立一個文藝組,上級文化部門就經(jīng)常有人下來輔導(dǎo)創(chuàng)作,我有時也去文藝組。有一次,《工農(nóng)兵》雜志的主編艾黎老師到來,他對我說:你那篇文章是夏濃同志幫你修改的,他說你的字漂亮,書寫也工整。
夏濃,這個名字我記住了。《工農(nóng)兵》的辦公地址在府城開元街,這年9月,我考進(jìn)廣東潮安高級中學(xué),校址在府城,就想開學(xué)后爭取去編輯部拜訪夏濃老師,但《工農(nóng)兵》卻遷往汕頭市去了。
此后,我在《工農(nóng)兵》上發(fā)了幾篇小說、散文,但無機(jī)會去汕頭。與夏濃老師首次見面,是我第一篇稿子發(fā)表的20年后。那時, 他已調(diào)到梅縣漢劇團(tuán)任編劇,我也在潮州市潮劇團(tuán)寫戲,一次出差梅縣,我初中同學(xué)李豐雄恰好在漢劇團(tuán)任舞美設(shè)計,就陪我去拜訪夏老師。
見面時由李豐雄作介紹,彼此的身份都是劇團(tuán)編劇,很平常,也沒客套話。但夏老師情緒不是很高,很平常地沖起工夫茶,說點(diǎn)寫戲的事。我提及他是我的第一個編輯老師,他點(diǎn)了點(diǎn)頭說:記得,你的稿子不是郵寄的,是你鄉(xiāng)一位作者送來的。
語氣很平淡、態(tài)度很平和。坐了一陣子,就告辭了。
不久,就聽說他已移居香港了。
1986年,我們在香港又見面了。
這年秋天,汕頭開通香港游,香港的友人邀我出去行一行。出發(fā)前,文友托我到香港時聯(lián)系夏濃老師,他有一批雜志要送汕頭,給了我電話和地址,我才知道夏老師在香港《華人》雜志社任職。
到達(dá)香港,接通電話,傳來的是他極熱情爽朗的聲音,直呼我的名字也分外親切,他說汕頭的朋友已通知我來香港找他的事,還說明可乘哪路電車,出發(fā)前告訴他,他可到車站接!普通的話語,句句令人溫暖。
約好時間,我與同行的妻子一道乘出租車,直達(dá)《華人》編輯部樓下,夏濃老師出現(xiàn)在大門口,手提一扎雜志,立即把我們夫婦接到近旁一家餐館。
他氣色很好,主動說及我給《工農(nóng)兵》寫稿的事,說我后來連續(xù)在那里發(fā)稿,他們把我作為重點(diǎn)作者培養(yǎng)。他說:可惜不久后,《工農(nóng)兵》停刊了。他又問及我的近況,還讓我有興趣可給他們的雜志寫稿。這次見面,與在梅縣初會,他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夏濃老師是我文學(xué)生涯的第一位接生婆,那篇幼稚的文章他是盡心作了刪改和潤色的,我一直心存感激。
我要感謝的第二位編輯師友是《汕頭日報》“韓江水”副刊的編輯陳煥展兄,他的特點(diǎn)是極認(rèn)真負(fù)責(zé),關(guān)心作者,常常給作者親筆回信,而不是通常那種通知采用與否的公文便箋。我從60年代至80年代,在那里發(fā)了許多小文章,因?yàn)樗嬖V我采用及發(fā)表日期,我有些自以為比較好的稿就直接寄他本人。
1960年我去林媽陂采訪大革命時期赤衛(wèi)隊(duì)的英勇機(jī)智故事,有一篇叫《不知姓名的老姆》他決定發(fā)表,而我在文末只寫了口述人:鄭木聲。他來信了解鄭木聲其人的政治面目,讓我在某日某時報紙付印之前去信告訴他。我一看,回信已來不及,又不敢用單位電話辦私人事,就專程跑到郵電局去掛號打長途電話告訴他:木聲伯是老赤衛(wèi)隊(duì)員,貧農(nóng)成份,接受采訪是大隊(duì)黨支部安排的。他這才放心。這件事讓我明白:文章千古事,白紙黑字,來不得半點(diǎn)馬虎。
煥展兄是位知名作家,他的作品早已發(fā)在《人民日報》及《萌芽》等全國性雜志上,他當(dāng)編輯絕不只是等米下鍋,他以培養(yǎng)作者為己任。他心中有一批重點(diǎn)業(yè)余作者,是他關(guān)注的對象。當(dāng)時,在潮安縣,李前忠、黃德林以及我這些人,應(yīng)該是他心中要幫助的對象。有一次,他要到潮安嫌水坑林場采訪,就約了我們?nèi)送小N耶?dāng)時在中學(xué)教書,為了能同行,他特地選在星期天。采訪回來,我們一起討論,定下文章架構(gòu),合作此文。他讓我先執(zhí)筆試寫。我熬夜寫出,天一亮交給他之后,就回學(xué)校上課了。
不久,文章發(fā)出來了,不單題目改了,文章幾乎全新重寫。我細(xì)細(xì)品讀,從題目《荒山拓林場》中,看到他重點(diǎn)在一個“拓”字,本意完全在寫林場工人的精神,不像我停留在寫景寫成績上。
受此啟發(fā),我重新回味那天受訪的場長,寫了一首不算短的詩:《山鷹——記一位林場場長》投給《羊城晚報》,在《花地》副刊上頭條發(fā)表了,年終還獲入選優(yōu)秀作品評選。
沒有煥展兄那個“拓”字,就沒有我的《山鷹》。
煥展兄,謝謝你!

來源|潮州日報
編輯|張澤慧
審核|詹樹鴻











